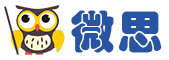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英国19世纪政治民主化进程.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4](p211).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4](p211).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