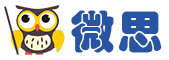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3文学基础"新史诗"什么意思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通常史诗的分类有两种,一是传统史诗(英雄史诗),又称原始史诗或民间史诗.主要作品有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两河流域的《吉尔迦美什史诗》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另一种是文学史诗(文人史诗),又称非原始史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但我想创造出另一种,个人的、自我的,为什么不可以?诗是原始的,它的语境比原始森林还古老,它的史性与生俱来.而我的史诗情结源于自我的神秘性,我甚至觉得,我一写诗,“我”可以在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如何激活,“我”所包含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容量,也只有史诗,可以帮助我蜕变更多过去的我将来的我.对于我而言,史诗,应是利刃的精神的通途,让诗意有血有肉地再一次经历触目惊心的现场,再一次忍受惊心动魄的命运.而诗人,也应是不断僭越语言边界的人,进入时间的中心,史仅为外衣,而诗为魂灵.对于我而言,史诗,不是大词,它仅是我一次前途未卜的语言探险,它寥廓,所以它更渺小,它深邃,所以它更浅薄.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诗人们一直对其畏途和恐高的所谓史诗,它低过你澎湃了的脑海.
我既非荷马,也不是但丁,但我也可以,规模我个人狂欢化的充满世界性的挽歌,仪式我个人癫狂化充满时空性的预言.凭什么?凭我革了自己的命.
与其说是史诗,不如说是新史诗,这将是创世纪的,试图重新唤醒华语之根系、中文之渊源,我的野心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不妄言也毋需去代表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只代表自己,而文本所带出的“宏大叙事”是迫不得已的史之惯性、时之擦痕,我也没必要去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类的大块头逐鹿中西,更没必要去与《诗经》和《九歌》决胜今古.中国之古体诗,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罕过二三千言外者.当然,史诗也不是比篇幅,《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那又怎样.而我的新史诗写作,只是我通向精神远景的一条隐秘通道,古和今被随时置换,地理和心理被随时挪移,而崛起的,永远是句子经过与超越后的闪耀.新史诗的真正身份,乃是它的无身而来的太阳一般的思想之美,它所挟带的不可阻挡的精神图腾,它必定会参与塑造全球视野和宇宙意识——以一个反复斗争的最低层的阴影的第三身份,它抵御着黑暗和光明对它的夹击.它突围人类的共识、梦想、信仰,它唯一,无身而来,抗拒着心灵的地震.而心灵早已成心灵史,所谓舍身取义,无身而来,刚刚好.暮古朝今读着我的诗,同时也是在读时光的诗——我想,这么说也是不为过的.在这种双重性中,“自我的同心圆”潜藏着超越语言的诗歌秘密.我妄想在《酒魂》就是营造这种新史诗的形态,追求一种全景式的容量,只为埋葬我五千年文化的宿命之身,和一颗小小的心.整体性的死,终于找到了诗的方法,全民性的尸,终于找到了史的方式.
对,新诗史,就是它了.那么,我想我可以宣告了,我以我的《酒魂》在 21 世纪一个新的历史时空交叉点上找到了新史诗的光圈.我正在走进、并移动这光圈,最后弃它而去.留一个孤兀的背影,够了.
《酒魂》所巨构的新史诗体系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酒魂》我写的不是酒文化,更不会为酒打广告,我只是“借酒还魂”,借酒精进入我血液后精神大醉灵魂却醒来的状态我想要说我的真话.而我,聆听历史,也愿意将自己的一颗头颅与几行诗被绳子捆在一起,让几行诗贴在头颅左耳的位置.我愿做惟一知道真相者,以我的醉态深入国家的小肠、历史的大肠.我要的是酒后──吐真言.例说《鸿门宴》,我的历史剧本之二至之八:夏狂人演义、老子演义、孔子演义、孟子演义、庄子演义、屈子演义、谪仙人演义,我完全将我对“诸子” 的“质疑”重新演义,我不完全迷信“圣人”,我要打破他们的思想对我(甚至是我们、历代囚在他们思想大牢的我们)的“笼罩”.这就是我的“酒魂”’之一种.我要思想洗牌后的千年之后的原生态,对,思想的原生态,这也是我的“醉态”之一种.但我又怎么能说我的思想优于前人或劣于古人?我应该可以在下个世纪甚至下十年成为一个思想家?或是大师?或是大诗人?这对我一丁点意义也没.这不,未写的历史又上轨了.这绝不是我所设想的下一步.但新史是可以提前预见.在创作方法上,我妄想我的《酒魂》是继承、深化和发展了史诗写作,并为新史诗写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希望我是中国史诗的最后一个诗人,现代新史诗的最初一个诗人,这是我的诗歌野心.
中国白话诗运动以来,海子写下《太阳•七部书》,罗振亚曾撰文说海子“实现了自郭沫若以来悬而未结的抒情史诗、现代史诗和东方史诗同构的夙愿,创造性地转换了史诗概念,创造出一种个人化的史诗形态”;我也不迷信海氏史诗,我的新史诗体系,是想重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精神补丁”,以对人类精神丧失和生存根本的承担为破碎的世界修复“生命漏洞”.我的新史诗体系,就是要史的大脑格式化重装系统,要诗的神经——挑起放置于整个人类历史——我一本书那般大小的孤独,跳脱于整个语言光驱、结束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刻录,创建全新、庞大、深远的思想备份,然后以此来消弭作为一个现代人回溯历史时间、独跋远古、洞察万端后的知识病毒,让新史进入时间的硬盘.所以我在《酒魂》用一个比喻说法,公猫在屋顶叫春,几只母猫闻声窜了过去,这样的力量抵得上任何伟大的诗歌.而听不到,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切:所谓不朽,所谓名声.所以我写诗像一棵被锯的大树,它位于过去的中间、未来的旁边,我让它倒下,它就还一声巨响,或更远处的某个王的棺木,甚至是留守儿童坐的小木凳,作为一个清醒的手艺人,它应该也懂得我要的是:重塑——我于是遇上一个属于我的怪圈——我用五万行诗来拖我思想的后腿,一直往前走一万年也未走到穷途未路,我用一首诗锯掉我大半生,一直锯到公元前一万年也未能将其锯断,这真是的怪圈中的怪圈.真,链锯砉砉.我锯掉了我的上半身,像地平线锯掉了苍天──我正在用月亮作鼠标,点击星空──启动银河作浏览器,只为进入我最最深邃最最黑暗的思想.所以对于我所提出的新诗史,我此刻还想提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诗歌概念:新诗史的砍头期.这显然也是一个比喻说法,并非要故意炮制不同凡响的论调.砍头.砍头.砍头.血淋淋的诗歌的头是我砍的.因为我这是对自己的时代谢罪,还有我不可一世的孤独,是毒手.再砍头.再砍头.再砍头.也别再说黄昏是刽子手,太阳的头是人的短视砍的——地平线就是因为人的视野局限性才诞生而思想的短见呢,诗人就只能砍永恒的头,他们的近视制造了无数几乎一模一样的的水平线,而永远看不见的东西,其实就囚禁在自己的身体里,是没人敢激活它而已,比如一套手机卡,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不激活它打它永远是个空号,激活了就有某个人在某地回应你.而我们还有什么没激活呢?除了灵魂还是灵魂.对于它,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可无人敢释放它.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它——人离开灵魂就会死.所以无人敢闯入死亡社区去放浪灵魂.来,我试范给你看,把它从脑门放出来,让禁锢它所有的国防线崩断,更要更要冲破世界性.如果夕阳西下,我掏出来一再灼伤的灵魂就是血性的夕阳,它替代成了我的天眼.如果能给宇宙关机,我就再重装它的系统我才再开机,打破星云结构,还有什么不可以打破,为了放灵魂出来,任何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比不上它的来得快,当它带我闯入死亡社区去突围时空.如果嫌太阳系这个内存容量太小,就换银河系,不够再换再换再换,而弹出的光驱,我投入公元八世纪的太阳就是大唐盛世,再投入公元十四至十七世纪就是文艺复兴,我完全可以发神经似的去过我喜欢的年代,我看见灵魂在诗行的那一头试范给我看看,哪哪,摁住这个鼠标.将这些曾经出现在《酒魂》的句子用来解围我的新史诗真有些蹩足.我开始写诗,当然也不存在新史诗的理念,这世界哪里有与生俱来的伟大的诗歌行动?世界上倒有很多没有答案或者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说,诗神为什么选择我写诗,我自幼无父无母,是与我隔了整整一甲子之龄的奶奶养大了我,我念完初中不忍奶奶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再挣钱供我上学,我下狠心辍学了.但奶奶又不让我南下打工,我呆在家就发疯似的写起诗来.诗神要求我学历吗?显然没有.诗神嫌我穷吗?更没有.但我疯狂写诗不务正业却让我奶奶的晚年过得更贫困,让我的妻儿至今犹未过上好生活,这是我的罪.诗是我悲壮的宿命吗?诗却真让我的孤独一直有我恰当的那个假想敌.要怎样无悔地说出这一段——无语的时候,诗神仍是光,一如坦承心海最晦暗的日出总是灰烬似的,疯狂,便总是通过苦恋者才变得无边的.我承受了诗神加之于我的比日子还大的孤独,和堪称怪诞的想象力,也尝到了诗神附体所带来的超出常人的个性,于我而言,我的身是自己的高山,我的灵魂是自己的流水,绝响于我所坚持的诗歌理想,十八年来我完全置身于诗歌圈子之外,孤独为我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华语谱系.在长达十多年的打工生涯我一直朝七点晚十一点超长时间的上班,在坐牢一样的上班时间,我的写作现场从未出现在宁静的书房,而是在闹市中我的收钱柜台上,我完全是在公共场合写作,嘈杂的空间,破碎的时间,我只能对抗着噪音和反灵感的去写诗.是诗歌,让我听到仅存的唯一的宁静.想想,在长达十八年的与中国诗界的隔离式隐身埋心地写自己的诗,写自己预订好的长达五万行甚至更长的《魂魄•九歌》,我一次次推迟了自己出道的时间,错过了70后诗人的队列,我甚至比90后还掉队,我在诗行之上流亡,但我的灵魂却得以独立于文本之上,至少我有这样的信念支撑着我孤独的诗心.在2011年之前,我的诗歌创作可以列出的履历几乎是零,我没有在任何刊物发表过作品,我这一大段留白,不是我没写,而是我呕心沥血的只顾写.这没什么不好.今天看来,这是厚积薄发.
《酒魂》所建构的新史诗体系来自我不可修改的“前半生”.
今天,大家看到的《酒魂》我自2005年就开始创作,直至 2013年5月才完稿,历时九年创作了这首近20万字的长诗.而这首长达1万行的《酒魂》仅是我《魂魄•九歌》的第一部.《魂魄•九歌》总十部,上卷分《酒魂》《诗魂》《人魂》,下卷分《山魄》《水魄》《月魄》《雪魄》《风魄》《鸟魄》,卷外《一个人的大合唱》,全诗总超5万行.
于我而言,新史诗,可以拆分为“新史”和“史诗”,“新史”是我心灵的图腾,“史诗”则是我灵魂的宗教.而我的图腾情怀是我生命中的疼痛符号所缕刻的墓志铭,我的宗教情怀则是疯狂头脑中的思想的通行证,我敢言,我是一个真正的以宗教和图腾的名义来写诗的诗人.那么,现在也可以这么说,《魂魄•九歌》所建构的新史诗体系,它是我个人宗教产生的重要根源,和对图腾交往、相通和结合的生动经历.必须承认,《酒魂》是神的舌尖、《诗魂》是道的身,《人魂》是佛的心,而《山魄》《水魄》《月魄》《雪魄》《风魄》《鸟魄》合成巫的千眼.神、佛、道、巫中的精华,缔造出了语言文字、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知识、理论、风俗、礼仪、习惯、人情、道德夹缝之中的一个诗人的经验、认识和耐心.为什么,由我来开启“一个人的新史” 框架的“个体生命的史诗表达”,难通乃我开启了“新史诗”写作的先河?
我写《酒魂》始终有个潜作者李白在与我同气同声,古时和今时如同一张罗网交织在一起,并以“一我”盘踞在古往今来的大寂寞之上,守猎“万我”,我就像古老文化中吐丝的新生蜘蛛,为力求“新史叙事”的完整性,而甘做自捕自囚拒绝大合唱的个性演义.我有我小小的角落,为大大的世界罗张一个圈套;我也有我小小的圆周,为长长的世纪围攻一个内心.所以,什么飞到我这都被一股气场粘住了.我妄想《酒魂》出来的效果完全是将新古典主义、大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以及神性写作、口语写作像干柴一般全加在一起的烈火涅槃而出的新诗体,所以我这首《酒魂》还有个特点,全诗所涉及的人名超过1000个以上,此外,地名、动物名、天文名词等也不计其数,如有人肯逐一统计,几乎每一项都创纪录.这首诗所动用的文体也无所不及,整部长诗并辅以诗剧的形式呈现的,甚至揉合了电影蒙太奇、剧本、小说、散文、古诗、书信、日记、舞台剧等所有文体,整首长诗至始至终都充满了色彩,音乐和立体感.是的,新史诗应有新史诗的胃口.
我想,在现代也该有个写现代诗的李白.很多读者都以为我玩穿越术,其然不然,所谓出入今古只是障眼法,这诗我是将所有时空挪移到一块了,大情怀来自大胸怀,似乎狂到把宇宙也捏在手心了,但又对这个国家斤斤计较,对这个社会种种不满,诗行到处十面埋伏和棉里藏针.我殚精竭虑地写《魂魄•九歌》,是想写一首中外古今一切诗歌的极限包容而又超出这一切独特地爆发出自己的精神小宇宙,并以此组成一个世界人文史和个人精神史同时并存的新秩序,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打通一条“无时间性”之路,以一个人精神受难的极限去完成回归最邃深内心“取诗经”的美学使命.
火车上的广播说,碎叶城到了
我下了车却是燕都怀集,来接车的不是我太太
变成了穿旗袍的肥环,这是什么鬼天气
我刚把眼镜摘下来,就忽下起古人所说的雪霰
这时,一个遥远的女音在我耳边喊:“小白!”
我揉了揉眼,久别重逢的却是民国时的情形
抬起腕表,一看,定格在1916年8月23日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肥环迎上与我拥抱
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不能太激动
身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我必须成为楷模
与这个绯闻女友的距离——中间隔着一个行李得了
这个行李装着我留洋回来的一箱乡愁
好了,不用翻了,还有不老的乡音
还有,乳名,两只蝴蝶的魂!
还有,还有一张大唐时的通关文牒!
我为此自豪——生平第一次.
面对这千古的第一大美女的香怀,我那
未经良好训练的白话诗又算得了什么
我不会扮演适之的,此刻我非常不适
我太白太白的心不会服从!但是无法校正的恍惚
来自,一个温软的女音在我耳边喊:“小白”
这是出自我《酒魂》“我的自传性线索之四”中的一节,是的,我无意充当什么“民族的代言人”或福柯所谓“普遍性的发言人”──不!这种过时的神话对我早已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我的自传性线索可以很多可以包含全人类的隐痛、追求、困扰、思考、梦幻、哭泣,所以在“我的自传性线索之四”我将“李白与胡适合体”后才充当我.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挟裹着一个精良的混编师,指挥着一台旷世的交响乐,率领着一个杰出的灵魂联合体”① .烂熟于胸的历史人物和典故在我笔下不断的翻新整合,那是出于某种大魂巨灵对我的召唤,就类似海子所言的“巨大的元素”,他们的不断肝胆出场和灵肉演义让我也觉得快要“涨破我的诗歌外壳”.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至此,我不由地觉得,“我的自传性线索”是前历史艺术修为的诗人身份的确认,这也就意味着,“诸神共舞”的世界像我一个人的狐邦狸国,固然诗意,但并不现实,甚至更加危险.反之,“诸神冲突”的世界固然灰暗,倒让我像一头集各家锋芒于一身的思想斗士,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认知的前提下,我才有超越“诸神之争”及其虚无主义的可能,还原为“一个诗人”的后历史艺术修养.所以我觉得不是创造神话,而是打破神话才是诗人的艺术行为.在我看来,一个诗人他应该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前进与革命路上的缩影.所以在“诸神共舞”的世界寻找“我的自传性线索”,是为了我的人文史“古老”,是的“古老”有起源之意,那就是要我的“诗心”回到诗意持续活动的胚胎状态,回到成人心灵生活中的童年期那样.而在“诸神冲突”的世界则是为了完成我的精神史考古,在这条孤绝路上,我进行的是大千世界之人、事、物驱遣裕的合体,让世人与我魂魄和济、声音共和,所以在我的美学概念,新史诗是我的人文史与精神史两者的同舟共济的探险前景,而这条海路可以看作是文字大合唱,舵手则是思想独唱.最终到达彼岸的,永远是一首诗篇,一个诗人.
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电梯间直降下来的辛亥,走出穿西装的太白
带着茫然多年的眼神走了几步,一拐弯
我接过了白话文的捧——我并没有参加革命
也没有参加独秀兄弟和大钊兄弟的新文化运动
树人兄弟也在写他的《狂人日记》,只有我吊儿郎当
我还与激进的五四、游行的青年们擦肩而过
我约了中文奥登、汉语波德莱尔,去对面街斗酒
隔着九十年,我不能用我的清醒救国
我就用我情绪激昂的醉态,做个“丑陋的中国人”
谁说我不爱国?“誓死力争,还我长安”我不屑说了
是我在进步,辫子我是一出世就没有
每当我头发稍长,奶奶就给五毛我,叫我剃光
我从小就代表我的光头,废除至高无上的
势力范围——我也太无法无天了——
“天子叫来不上课”,呃,我是转校了——
我也积极支持“改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
也师从约翰•杜威(不信?你去问嗣穈)
但要我终生服膺实验主义(pragmatism)哲学,傻逼呀,我一贪杯
连上帝也不服了,“喂,今年是到了哪年?”
一醉我就恢复了李白的脸,再一摆手
我就有了提着宇宙这个空酒杯甩门而出的疯劲——
[可能的进行曲]
从唐朝飞到民国共要九个多小时,
抵达民国后,我伸出右手就是一座大桥
再左手在上面一捋,就能搭上热血沸腾的火车
我随身携带中国象棋,在紧要关头我随手掏出一辆马车
与一个谋士,我无力拯救世界或人民
只能出神入化给自己一个致命的
场合.哪哪,在这里,在这里,我可以顺血管逆流而上
坐三小时渡轮回到心海,再通过一场酒气
飞到脑海的荒岛.我并不是来这避世
而是测试我有没有把世界翻过来的勇气
再把时空倒扣过来,缩小,让我胸有成城,城中有国
再想下去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
我是上下五千年的王,如大梦初醒
临睡前我将我的身体刚好摆好成一盘中国象棋
这不,醒来,发觉少了一车一仕
左心房空了,右心房也空了
咦,我整颗心不见了
海子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至于我的诗歌理想,如果有那就是,不断的在诗行之上寻找属于“我的自传性线索”?我的诗歌血统似有现代派古人的“新野性”,古老中国一直是我心理上的故乡,它的“古老性”乃我身的“出生地”,而“新野性”则是我心的栖居地.我在诗中也反复强调了我的“新野性”的存在:“如果可以,不必是书房,请把我关在牢房——才让我写诗.我没有资格当政治犯,那请把我当成强奸犯,并请看守好我这头文化动物中最生猛的诗歌畜生.我的可耻之处就是对语言使用了暴力,我的灵魂像头性饥饿的公牛,一碰见灵感就扑上去,我犯下了给诗歌非法配种的滔天大罪,我为这个文明古国贡献了二十三头四不像的文体野种,如果可以,请逮捕我的思想,它才是幕后真凶,但它来无影去无踪.卫星也不能跟踪它匪夷所思的思路,但我可为你们提供它骇人听闻的作案手段,比如,想象力驱动的坦克,意象密集的空袭.难道非要我树敌吗.古,今,中,外,就是这牢狱我所要面对的四堵高墙,如果我没有资格当一个伟大的诗人,那就让我当一个千古的诗囚——把牢底坐穿,顿悟万岁如果可以,不必是佛法,让我学会魔法——我这就来以身试诗,并来领受这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诗刑.”所以我在诗中呼喊隔着历史我不能用我的清醒救国我就用我情绪激昂的醉态做个“丑陋的中国人”,我也许并不是先锋,但我在诗行简直就是在冲锋.我更不会是猛士,但我在诗行之上不断寻找属于“我的自传性线索”来考察“新史诗”的马力,在魂魄的边界,把自己逼进了体能和智力的创作极限状态,等待一首大诗吊诡般的出现.
通常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而我的“新史诗”,只是寻找“我的自传性线索”的个人史演化规律,去展示整个人类历史的创世过程,去构筑“新史诗”的全新体系.《酒魂》是我《魂魄•九歌》开卷之作,它肯定充满了探索和实验性,它也是我提出“新史诗”体系的实践文本.确实《酒魂》让我冲击了新一轮到来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史诗”给“新史诗”所下的判词.《魂魄•九歌》它必须以“史诗”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去进行,然而,问题依然是,《酒魂》所走出“新史诗”的步伐也是我始料未及.我对“史”与“诗”的关系也许是一对老夫妻,但“新史诗”的出现,它目前就可能是他们的“孤儿”.从来就没有伟大的时刻,只有历史性时刻,如果《酒魂》不能在属于它的历史性时刻醉了,那么它所有句子的醉酒行为都只白费了历史的豪肠.而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近代诗歌史几乎就没有“史诗”的年代,突然冒出来“新史诗”这匹黑马,也并非我强加妄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知道,谁从这个命名谁从这个命名中得到好处,谁则受到这个命名的压迫.不过我很高兴在这分享自己的《酒魂》所幻化出来的产物:新史诗.
但我想创造出另一种,个人的、自我的,为什么不可以?诗是原始的,它的语境比原始森林还古老,它的史性与生俱来.而我的史诗情结源于自我的神秘性,我甚至觉得,我一写诗,“我”可以在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如何激活,“我”所包含的巨大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容量,也只有史诗,可以帮助我蜕变更多过去的我将来的我.对于我而言,史诗,应是利刃的精神的通途,让诗意有血有肉地再一次经历触目惊心的现场,再一次忍受惊心动魄的命运.而诗人,也应是不断僭越语言边界的人,进入时间的中心,史仅为外衣,而诗为魂灵.对于我而言,史诗,不是大词,它仅是我一次前途未卜的语言探险,它寥廓,所以它更渺小,它深邃,所以它更浅薄.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诗人们一直对其畏途和恐高的所谓史诗,它低过你澎湃了的脑海.
我既非荷马,也不是但丁,但我也可以,规模我个人狂欢化的充满世界性的挽歌,仪式我个人癫狂化充满时空性的预言.凭什么?凭我革了自己的命.
与其说是史诗,不如说是新史诗,这将是创世纪的,试图重新唤醒华语之根系、中文之渊源,我的野心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不妄言也毋需去代表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只代表自己,而文本所带出的“宏大叙事”是迫不得已的史之惯性、时之擦痕,我也没必要去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类的大块头逐鹿中西,更没必要去与《诗经》和《九歌》决胜今古.中国之古体诗,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罕过二三千言外者.当然,史诗也不是比篇幅,《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那又怎样.而我的新史诗写作,只是我通向精神远景的一条隐秘通道,古和今被随时置换,地理和心理被随时挪移,而崛起的,永远是句子经过与超越后的闪耀.新史诗的真正身份,乃是它的无身而来的太阳一般的思想之美,它所挟带的不可阻挡的精神图腾,它必定会参与塑造全球视野和宇宙意识——以一个反复斗争的最低层的阴影的第三身份,它抵御着黑暗和光明对它的夹击.它突围人类的共识、梦想、信仰,它唯一,无身而来,抗拒着心灵的地震.而心灵早已成心灵史,所谓舍身取义,无身而来,刚刚好.暮古朝今读着我的诗,同时也是在读时光的诗——我想,这么说也是不为过的.在这种双重性中,“自我的同心圆”潜藏着超越语言的诗歌秘密.我妄想在《酒魂》就是营造这种新史诗的形态,追求一种全景式的容量,只为埋葬我五千年文化的宿命之身,和一颗小小的心.整体性的死,终于找到了诗的方法,全民性的尸,终于找到了史的方式.
对,新诗史,就是它了.那么,我想我可以宣告了,我以我的《酒魂》在 21 世纪一个新的历史时空交叉点上找到了新史诗的光圈.我正在走进、并移动这光圈,最后弃它而去.留一个孤兀的背影,够了.
《酒魂》所巨构的新史诗体系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酒魂》我写的不是酒文化,更不会为酒打广告,我只是“借酒还魂”,借酒精进入我血液后精神大醉灵魂却醒来的状态我想要说我的真话.而我,聆听历史,也愿意将自己的一颗头颅与几行诗被绳子捆在一起,让几行诗贴在头颅左耳的位置.我愿做惟一知道真相者,以我的醉态深入国家的小肠、历史的大肠.我要的是酒后──吐真言.例说《鸿门宴》,我的历史剧本之二至之八:夏狂人演义、老子演义、孔子演义、孟子演义、庄子演义、屈子演义、谪仙人演义,我完全将我对“诸子” 的“质疑”重新演义,我不完全迷信“圣人”,我要打破他们的思想对我(甚至是我们、历代囚在他们思想大牢的我们)的“笼罩”.这就是我的“酒魂”’之一种.我要思想洗牌后的千年之后的原生态,对,思想的原生态,这也是我的“醉态”之一种.但我又怎么能说我的思想优于前人或劣于古人?我应该可以在下个世纪甚至下十年成为一个思想家?或是大师?或是大诗人?这对我一丁点意义也没.这不,未写的历史又上轨了.这绝不是我所设想的下一步.但新史是可以提前预见.在创作方法上,我妄想我的《酒魂》是继承、深化和发展了史诗写作,并为新史诗写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希望我是中国史诗的最后一个诗人,现代新史诗的最初一个诗人,这是我的诗歌野心.
中国白话诗运动以来,海子写下《太阳•七部书》,罗振亚曾撰文说海子“实现了自郭沫若以来悬而未结的抒情史诗、现代史诗和东方史诗同构的夙愿,创造性地转换了史诗概念,创造出一种个人化的史诗形态”;我也不迷信海氏史诗,我的新史诗体系,是想重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精神补丁”,以对人类精神丧失和生存根本的承担为破碎的世界修复“生命漏洞”.我的新史诗体系,就是要史的大脑格式化重装系统,要诗的神经——挑起放置于整个人类历史——我一本书那般大小的孤独,跳脱于整个语言光驱、结束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刻录,创建全新、庞大、深远的思想备份,然后以此来消弭作为一个现代人回溯历史时间、独跋远古、洞察万端后的知识病毒,让新史进入时间的硬盘.所以我在《酒魂》用一个比喻说法,公猫在屋顶叫春,几只母猫闻声窜了过去,这样的力量抵得上任何伟大的诗歌.而听不到,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切:所谓不朽,所谓名声.所以我写诗像一棵被锯的大树,它位于过去的中间、未来的旁边,我让它倒下,它就还一声巨响,或更远处的某个王的棺木,甚至是留守儿童坐的小木凳,作为一个清醒的手艺人,它应该也懂得我要的是:重塑——我于是遇上一个属于我的怪圈——我用五万行诗来拖我思想的后腿,一直往前走一万年也未走到穷途未路,我用一首诗锯掉我大半生,一直锯到公元前一万年也未能将其锯断,这真是的怪圈中的怪圈.真,链锯砉砉.我锯掉了我的上半身,像地平线锯掉了苍天──我正在用月亮作鼠标,点击星空──启动银河作浏览器,只为进入我最最深邃最最黑暗的思想.所以对于我所提出的新诗史,我此刻还想提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诗歌概念:新诗史的砍头期.这显然也是一个比喻说法,并非要故意炮制不同凡响的论调.砍头.砍头.砍头.血淋淋的诗歌的头是我砍的.因为我这是对自己的时代谢罪,还有我不可一世的孤独,是毒手.再砍头.再砍头.再砍头.也别再说黄昏是刽子手,太阳的头是人的短视砍的——地平线就是因为人的视野局限性才诞生而思想的短见呢,诗人就只能砍永恒的头,他们的近视制造了无数几乎一模一样的的水平线,而永远看不见的东西,其实就囚禁在自己的身体里,是没人敢激活它而已,比如一套手机卡,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不激活它打它永远是个空号,激活了就有某个人在某地回应你.而我们还有什么没激活呢?除了灵魂还是灵魂.对于它,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可无人敢释放它.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它——人离开灵魂就会死.所以无人敢闯入死亡社区去放浪灵魂.来,我试范给你看,把它从脑门放出来,让禁锢它所有的国防线崩断,更要更要冲破世界性.如果夕阳西下,我掏出来一再灼伤的灵魂就是血性的夕阳,它替代成了我的天眼.如果能给宇宙关机,我就再重装它的系统我才再开机,打破星云结构,还有什么不可以打破,为了放灵魂出来,任何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比不上它的来得快,当它带我闯入死亡社区去突围时空.如果嫌太阳系这个内存容量太小,就换银河系,不够再换再换再换,而弹出的光驱,我投入公元八世纪的太阳就是大唐盛世,再投入公元十四至十七世纪就是文艺复兴,我完全可以发神经似的去过我喜欢的年代,我看见灵魂在诗行的那一头试范给我看看,哪哪,摁住这个鼠标.将这些曾经出现在《酒魂》的句子用来解围我的新史诗真有些蹩足.我开始写诗,当然也不存在新史诗的理念,这世界哪里有与生俱来的伟大的诗歌行动?世界上倒有很多没有答案或者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说,诗神为什么选择我写诗,我自幼无父无母,是与我隔了整整一甲子之龄的奶奶养大了我,我念完初中不忍奶奶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再挣钱供我上学,我下狠心辍学了.但奶奶又不让我南下打工,我呆在家就发疯似的写起诗来.诗神要求我学历吗?显然没有.诗神嫌我穷吗?更没有.但我疯狂写诗不务正业却让我奶奶的晚年过得更贫困,让我的妻儿至今犹未过上好生活,这是我的罪.诗是我悲壮的宿命吗?诗却真让我的孤独一直有我恰当的那个假想敌.要怎样无悔地说出这一段——无语的时候,诗神仍是光,一如坦承心海最晦暗的日出总是灰烬似的,疯狂,便总是通过苦恋者才变得无边的.我承受了诗神加之于我的比日子还大的孤独,和堪称怪诞的想象力,也尝到了诗神附体所带来的超出常人的个性,于我而言,我的身是自己的高山,我的灵魂是自己的流水,绝响于我所坚持的诗歌理想,十八年来我完全置身于诗歌圈子之外,孤独为我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华语谱系.在长达十多年的打工生涯我一直朝七点晚十一点超长时间的上班,在坐牢一样的上班时间,我的写作现场从未出现在宁静的书房,而是在闹市中我的收钱柜台上,我完全是在公共场合写作,嘈杂的空间,破碎的时间,我只能对抗着噪音和反灵感的去写诗.是诗歌,让我听到仅存的唯一的宁静.想想,在长达十八年的与中国诗界的隔离式隐身埋心地写自己的诗,写自己预订好的长达五万行甚至更长的《魂魄•九歌》,我一次次推迟了自己出道的时间,错过了70后诗人的队列,我甚至比90后还掉队,我在诗行之上流亡,但我的灵魂却得以独立于文本之上,至少我有这样的信念支撑着我孤独的诗心.在2011年之前,我的诗歌创作可以列出的履历几乎是零,我没有在任何刊物发表过作品,我这一大段留白,不是我没写,而是我呕心沥血的只顾写.这没什么不好.今天看来,这是厚积薄发.
《酒魂》所建构的新史诗体系来自我不可修改的“前半生”.
今天,大家看到的《酒魂》我自2005年就开始创作,直至 2013年5月才完稿,历时九年创作了这首近20万字的长诗.而这首长达1万行的《酒魂》仅是我《魂魄•九歌》的第一部.《魂魄•九歌》总十部,上卷分《酒魂》《诗魂》《人魂》,下卷分《山魄》《水魄》《月魄》《雪魄》《风魄》《鸟魄》,卷外《一个人的大合唱》,全诗总超5万行.
于我而言,新史诗,可以拆分为“新史”和“史诗”,“新史”是我心灵的图腾,“史诗”则是我灵魂的宗教.而我的图腾情怀是我生命中的疼痛符号所缕刻的墓志铭,我的宗教情怀则是疯狂头脑中的思想的通行证,我敢言,我是一个真正的以宗教和图腾的名义来写诗的诗人.那么,现在也可以这么说,《魂魄•九歌》所建构的新史诗体系,它是我个人宗教产生的重要根源,和对图腾交往、相通和结合的生动经历.必须承认,《酒魂》是神的舌尖、《诗魂》是道的身,《人魂》是佛的心,而《山魄》《水魄》《月魄》《雪魄》《风魄》《鸟魄》合成巫的千眼.神、佛、道、巫中的精华,缔造出了语言文字、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知识、理论、风俗、礼仪、习惯、人情、道德夹缝之中的一个诗人的经验、认识和耐心.为什么,由我来开启“一个人的新史” 框架的“个体生命的史诗表达”,难通乃我开启了“新史诗”写作的先河?
我写《酒魂》始终有个潜作者李白在与我同气同声,古时和今时如同一张罗网交织在一起,并以“一我”盘踞在古往今来的大寂寞之上,守猎“万我”,我就像古老文化中吐丝的新生蜘蛛,为力求“新史叙事”的完整性,而甘做自捕自囚拒绝大合唱的个性演义.我有我小小的角落,为大大的世界罗张一个圈套;我也有我小小的圆周,为长长的世纪围攻一个内心.所以,什么飞到我这都被一股气场粘住了.我妄想《酒魂》出来的效果完全是将新古典主义、大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以及神性写作、口语写作像干柴一般全加在一起的烈火涅槃而出的新诗体,所以我这首《酒魂》还有个特点,全诗所涉及的人名超过1000个以上,此外,地名、动物名、天文名词等也不计其数,如有人肯逐一统计,几乎每一项都创纪录.这首诗所动用的文体也无所不及,整部长诗并辅以诗剧的形式呈现的,甚至揉合了电影蒙太奇、剧本、小说、散文、古诗、书信、日记、舞台剧等所有文体,整首长诗至始至终都充满了色彩,音乐和立体感.是的,新史诗应有新史诗的胃口.
我想,在现代也该有个写现代诗的李白.很多读者都以为我玩穿越术,其然不然,所谓出入今古只是障眼法,这诗我是将所有时空挪移到一块了,大情怀来自大胸怀,似乎狂到把宇宙也捏在手心了,但又对这个国家斤斤计较,对这个社会种种不满,诗行到处十面埋伏和棉里藏针.我殚精竭虑地写《魂魄•九歌》,是想写一首中外古今一切诗歌的极限包容而又超出这一切独特地爆发出自己的精神小宇宙,并以此组成一个世界人文史和个人精神史同时并存的新秩序,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打通一条“无时间性”之路,以一个人精神受难的极限去完成回归最邃深内心“取诗经”的美学使命.
火车上的广播说,碎叶城到了
我下了车却是燕都怀集,来接车的不是我太太
变成了穿旗袍的肥环,这是什么鬼天气
我刚把眼镜摘下来,就忽下起古人所说的雪霰
这时,一个遥远的女音在我耳边喊:“小白!”
我揉了揉眼,久别重逢的却是民国时的情形
抬起腕表,一看,定格在1916年8月23日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肥环迎上与我拥抱
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不能太激动
身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我必须成为楷模
与这个绯闻女友的距离——中间隔着一个行李得了
这个行李装着我留洋回来的一箱乡愁
好了,不用翻了,还有不老的乡音
还有,乳名,两只蝴蝶的魂!
还有,还有一张大唐时的通关文牒!
我为此自豪——生平第一次.
面对这千古的第一大美女的香怀,我那
未经良好训练的白话诗又算得了什么
我不会扮演适之的,此刻我非常不适
我太白太白的心不会服从!但是无法校正的恍惚
来自,一个温软的女音在我耳边喊:“小白”
这是出自我《酒魂》“我的自传性线索之四”中的一节,是的,我无意充当什么“民族的代言人”或福柯所谓“普遍性的发言人”──不!这种过时的神话对我早已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我的自传性线索可以很多可以包含全人类的隐痛、追求、困扰、思考、梦幻、哭泣,所以在“我的自传性线索之四”我将“李白与胡适合体”后才充当我.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挟裹着一个精良的混编师,指挥着一台旷世的交响乐,率领着一个杰出的灵魂联合体”① .烂熟于胸的历史人物和典故在我笔下不断的翻新整合,那是出于某种大魂巨灵对我的召唤,就类似海子所言的“巨大的元素”,他们的不断肝胆出场和灵肉演义让我也觉得快要“涨破我的诗歌外壳”.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至此,我不由地觉得,“我的自传性线索”是前历史艺术修为的诗人身份的确认,这也就意味着,“诸神共舞”的世界像我一个人的狐邦狸国,固然诗意,但并不现实,甚至更加危险.反之,“诸神冲突”的世界固然灰暗,倒让我像一头集各家锋芒于一身的思想斗士,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认知的前提下,我才有超越“诸神之争”及其虚无主义的可能,还原为“一个诗人”的后历史艺术修养.所以我觉得不是创造神话,而是打破神话才是诗人的艺术行为.在我看来,一个诗人他应该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前进与革命路上的缩影.所以在“诸神共舞”的世界寻找“我的自传性线索”,是为了我的人文史“古老”,是的“古老”有起源之意,那就是要我的“诗心”回到诗意持续活动的胚胎状态,回到成人心灵生活中的童年期那样.而在“诸神冲突”的世界则是为了完成我的精神史考古,在这条孤绝路上,我进行的是大千世界之人、事、物驱遣裕的合体,让世人与我魂魄和济、声音共和,所以在我的美学概念,新史诗是我的人文史与精神史两者的同舟共济的探险前景,而这条海路可以看作是文字大合唱,舵手则是思想独唱.最终到达彼岸的,永远是一首诗篇,一个诗人.
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电梯间直降下来的辛亥,走出穿西装的太白
带着茫然多年的眼神走了几步,一拐弯
我接过了白话文的捧——我并没有参加革命
也没有参加独秀兄弟和大钊兄弟的新文化运动
树人兄弟也在写他的《狂人日记》,只有我吊儿郎当
我还与激进的五四、游行的青年们擦肩而过
我约了中文奥登、汉语波德莱尔,去对面街斗酒
隔着九十年,我不能用我的清醒救国
我就用我情绪激昂的醉态,做个“丑陋的中国人”
谁说我不爱国?“誓死力争,还我长安”我不屑说了
是我在进步,辫子我是一出世就没有
每当我头发稍长,奶奶就给五毛我,叫我剃光
我从小就代表我的光头,废除至高无上的
势力范围——我也太无法无天了——
“天子叫来不上课”,呃,我是转校了——
我也积极支持“改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
也师从约翰•杜威(不信?你去问嗣穈)
但要我终生服膺实验主义(pragmatism)哲学,傻逼呀,我一贪杯
连上帝也不服了,“喂,今年是到了哪年?”
一醉我就恢复了李白的脸,再一摆手
我就有了提着宇宙这个空酒杯甩门而出的疯劲——
[可能的进行曲]
从唐朝飞到民国共要九个多小时,
抵达民国后,我伸出右手就是一座大桥
再左手在上面一捋,就能搭上热血沸腾的火车
我随身携带中国象棋,在紧要关头我随手掏出一辆马车
与一个谋士,我无力拯救世界或人民
只能出神入化给自己一个致命的
场合.哪哪,在这里,在这里,我可以顺血管逆流而上
坐三小时渡轮回到心海,再通过一场酒气
飞到脑海的荒岛.我并不是来这避世
而是测试我有没有把世界翻过来的勇气
再把时空倒扣过来,缩小,让我胸有成城,城中有国
再想下去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
我是上下五千年的王,如大梦初醒
临睡前我将我的身体刚好摆好成一盘中国象棋
这不,醒来,发觉少了一车一仕
左心房空了,右心房也空了
咦,我整颗心不见了
海子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至于我的诗歌理想,如果有那就是,不断的在诗行之上寻找属于“我的自传性线索”?我的诗歌血统似有现代派古人的“新野性”,古老中国一直是我心理上的故乡,它的“古老性”乃我身的“出生地”,而“新野性”则是我心的栖居地.我在诗中也反复强调了我的“新野性”的存在:“如果可以,不必是书房,请把我关在牢房——才让我写诗.我没有资格当政治犯,那请把我当成强奸犯,并请看守好我这头文化动物中最生猛的诗歌畜生.我的可耻之处就是对语言使用了暴力,我的灵魂像头性饥饿的公牛,一碰见灵感就扑上去,我犯下了给诗歌非法配种的滔天大罪,我为这个文明古国贡献了二十三头四不像的文体野种,如果可以,请逮捕我的思想,它才是幕后真凶,但它来无影去无踪.卫星也不能跟踪它匪夷所思的思路,但我可为你们提供它骇人听闻的作案手段,比如,想象力驱动的坦克,意象密集的空袭.难道非要我树敌吗.古,今,中,外,就是这牢狱我所要面对的四堵高墙,如果我没有资格当一个伟大的诗人,那就让我当一个千古的诗囚——把牢底坐穿,顿悟万岁如果可以,不必是佛法,让我学会魔法——我这就来以身试诗,并来领受这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诗刑.”所以我在诗中呼喊隔着历史我不能用我的清醒救国我就用我情绪激昂的醉态做个“丑陋的中国人”,我也许并不是先锋,但我在诗行简直就是在冲锋.我更不会是猛士,但我在诗行之上不断寻找属于“我的自传性线索”来考察“新史诗”的马力,在魂魄的边界,把自己逼进了体能和智力的创作极限状态,等待一首大诗吊诡般的出现.
通常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而我的“新史诗”,只是寻找“我的自传性线索”的个人史演化规律,去展示整个人类历史的创世过程,去构筑“新史诗”的全新体系.《酒魂》是我《魂魄•九歌》开卷之作,它肯定充满了探索和实验性,它也是我提出“新史诗”体系的实践文本.确实《酒魂》让我冲击了新一轮到来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史诗”给“新史诗”所下的判词.《魂魄•九歌》它必须以“史诗”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去进行,然而,问题依然是,《酒魂》所走出“新史诗”的步伐也是我始料未及.我对“史”与“诗”的关系也许是一对老夫妻,但“新史诗”的出现,它目前就可能是他们的“孤儿”.从来就没有伟大的时刻,只有历史性时刻,如果《酒魂》不能在属于它的历史性时刻醉了,那么它所有句子的醉酒行为都只白费了历史的豪肠.而我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近代诗歌史几乎就没有“史诗”的年代,突然冒出来“新史诗”这匹黑马,也并非我强加妄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知道,谁从这个命名谁从这个命名中得到好处,谁则受到这个命名的压迫.不过我很高兴在这分享自己的《酒魂》所幻化出来的产物:新史诗.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