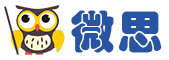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白种人眼中的黄种人?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19世纪早期,只有零星的中国移民进入澳洲,那时候可以选择的职业是做牧羊人、厨子和农场苦力.19世纪30年代由于牧羊业发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做出决定,开始雇佣华工,50年代发现金矿,澳大利亚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吸引了广东省省会附近13个县的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到1890年在澳洲的华人大约有4.9万人,大家都知道旧金山指的是美国的三藩市,而新金山墨尔本则鲜为人知.
13个县的移民都讲同一种方言,具有相似的体型、思想和性格,在当地人眼中,华人移民朴素、和蔼、热爱和平、勤奋且节俭,但也有不良嗜好,比如抽鸦片和赌博.他们崇拜偶像,带来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信仰,在金矿区修了很多庙宇.他们的语言、衣着和留的辫子,习惯和癖好,风俗和传统生活方式都同当地人不同.
中国人的出现潜在的威胁到了“白色澳洲”的现实,欧洲白人被中国人的出现和成功吓坏了.“白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华人矿工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的惊恐、怀疑和误解.当时为了调查劳工情况,新南威尔士成立了一个移民调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认为苦力移民会降低白人的生活水平,要求限制移民.
1857年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就写道:“先不考虑中国人带给金矿区的麻风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可怕的病带到哪里——就单单从他们心智低下,身体瘦弱,生活习俗半野蛮化的角度来看,我就反对让他们进入澳洲,他们完全不配融入我们这么文明开化的国家,我要问问大家,他们这些偶像崇拜者能够让我们的基督信仰纯洁吗?这些杏核眼、黄皮肤的东方人能改进我们的种族吗?这些从天朝带来的习性和邪恶能够推动澳大利亚吗?完全不能……”
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念弥漫着整个19世纪晚期,影响着当时的移民立法,1901年澳大利亚移民入国法案就是这种“白色澳大利亚”政策的集中体现,该法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限制非欧洲人来澳大利亚定居.而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对每一个想移民的人强制进行某一种欧洲语言的听写测试,只有特别豁免者除外.豁免证书是经澳大利亚外交部批准,由澳大利亚海关颁发的允许外国人移民澳洲的特别通行证.
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在金矿和锡矿开采殆尽之后,固守落叶归根的中国人很多又回到了祖国,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数急剧下落.尽管危机四伏,也有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扎下了根,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人脉关系,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忍辱负重并且灵活圆滑得面对和处理周围随时出现的敌视.这些定居的中国人,在当地建立家庭,繁衍生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续移民
19世纪50年代发现金矿,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发现锡矿之后,很多华人聚集到新南威尔士的北部高原地区.189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华人占到当地人口的11%,这是华人人数的最高峰,随后锡矿越来越少,很多华人或者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回国,当地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从1891年的1300人下降到1901年的593人,而1921年是169人,到了1947年只有47人了,不过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新人到来了.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赞助亲戚或乡邻移民过来.
在当地华人中,帕西·杨的故事广为流传,足以代表华人移民的努力、辛劳和聪明才智.澳大利亚光兴百货公司(Kwong Sing store)的奠基人帕西·杨1865年出生在广东中山石歧的村庄里,大约20岁的时候通过同村人的关系来到了澳大利亚,随后10年里杨在不同的华人开的店铺打工,生活颠沛流离,10年中的大部分岁月他都在新南威尔士的乡村度过.虽然偶尔也回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在澳洲.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人介绍,帕西·杨来到位于新南威尔士格伦因斯(Glen Innes)地区的光兴商店工作.1907年杨成了光兴的股东之一,到了1912年他几乎接管了光兴,成为了主要的股东和管理者.杨的孩子们相继在澳大利亚出生,他还赞助自己的侄子一个接一个从中国老家来到澳洲他的店铺里工作.不久他的子侄们又一个个的另立门户,开办了自己的店铺,并且相继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帕西·杨家族移民澳洲的活动都发生在1901年移民法实施之后,杨和其他南部高原地区的小业主一样,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让亲戚们陆续来到澳洲,并且想方设法让他们定居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律规定,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并且通过经商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华人可以雇佣中国出生的店员,可以让这些店员暂住一段时期.
伊莱恩·江的父母在滕特菲尔德镇经营商铺,她回忆父母利用人脉关系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亲戚和乡邻服务,这些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进行.他说,“我认为我的父母认识悉尼某些签发移民证的人,他给这些人写信,把某个店铺需要的店员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我父亲把一些人带出来的方法,当然也有别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是主要的.”
一个店铺能雇佣多少中国出生的店员,澳大利亚的法律对此是有规定的,这就刺激华人商店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断扩张,南部高原地区的华人店铺都是如此.因为开办的店铺越多,能够把亲戚带出来的机会就越多.滕特菲尔德镇上的洪源店创立于1899年,到了1915年该店的主要股东和管理者是哈瑞·费,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山石歧的老家度过的,到了30年代,洪源已经在镇上开办了另外3个小商店,在附近村镇有了3个分店和两个零售自助店.
定居华人希望把亲友带出来,为他们的果园、店铺和工厂补充新的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华工,有些人就冒险采取非法的手段,非法移民多由香港商人组织.这些非法移民遭受到难以想象的痛苦.有的人藏在甲板下的货舱、米箱里,整个旅程不见天日,有不少人因窒息而死亡.1905年在悉尼的一艘德国船里发现了23个偷渡客,这些人后来被罚到德属新几内亚做一年苦工.
扎根
华人所采取的谋生方式十分相似,他们主要集中在工业、商业和初级产品生产等领域.多数华人种植蔬菜,菜农本身也是小贩,在清晨5点挑菜到市场,在城市里走街串巷叫卖新鲜蔬菜的华人也很常见.
华人零售店开始营业可以追溯到淘金热,开始主要经营中国货物,大米、丝绸、茶叶、瓷器和生姜等.20世纪前20年中,新南威尔士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牛油、面粉、皮草、金条、铅、煤和木材.出口贸易一半控制在华人手里.1906 年,新南威尔士水果交易所主席断言:香蕉贸易已经从英国人手里转到华人手中.同样的警告不时出现在报纸上.到1921年为止悉尼的许多老牌华人水果商行,永生、泰生、永安都经营香蕉.在墨尔本,添杨、雷鹏和荣享是著名的香蕉和西红柿经销商.华商兴旺发达的例证之一是1917年成立了拥有实际资本10.8万镑的中澳船行,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零售店、食品杂货铺和进出口贸易行都对船行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大多数华人移民与他们的家乡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感情联系.在20世纪前20年中,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的企业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开办起来.这些企业包括制造厂、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以及百货公司.在所有投资和投机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由新南威尔士华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在悉尼的白人公司的帮助下建立,华人创办了三家大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和新安,随后这个商业帝国扩展到远东.过去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是这三家开办的.
华人的成功不可避免的引来白人的不满,澳大利亚作家玛丽·贡特(1861-1942年)在《一个女人在中国》里回忆早年在澳洲的生活经历时说:“我曾多次看到不幸的中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到我父亲家来寻求保护.那些我们称之为流氓的街头恶棍不问情由,任何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往他身上扔石头.”
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还源于经济竞争.以家具制造为例,19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华人靠制作廉价和低档家具谋生,主要制作椅子,货架、脸盆、碗橱和桌子.本土欧洲工匠则垄断了价格高昂的家具.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欧洲人也不得不制造低档产品时,他们发现华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行业.欧洲工匠开始鼓动政府当局,禁止华工移民.他们要求限制华工的劳动时间,并在产品上标明是由白人还是华人制作的,鼓励白人购买白人的商品.面对澳洲同行的打压,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社团,筹措经费游说议员,并聘请律师.1913年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会诞生.
“白澳政策”反而使华人移民变得更团结,更有民族意识.1901年只有少数华人反对移民法,1905年新南威尔士已经召开了州际性质的华人大会商讨共同面对的问题.会议讨论5类华人(商人、官员、传教士、学生和旅游者)入境问题,并为设立中国总领事馆而努力.
劳工阶层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商人少一般都很富裕,并在华人的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上起领导作用,梅光达便是华人中杰出的领导之一.梅光达1850年生于台山市端芬镇山底村龙腾里,9岁时随叔父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拉顿金矿“淘金”.他先是在白人的杂货店里做杂工.因聪明伶俐,被白人金矿主收为养子.1871年,梅光达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1877年养父病逝后继承了养父的产业.之后迁居悉尼,从事商贸活动,专营中国茶叶、丝绸及饮食,很快成为名倾悉尼的华人大富商.1887年5月至8月,清廷派总兵王荣和以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以调查华民商务的名义,到达悉尼、墨尔本等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王、余抵达悉尼时,梅光达亲自率领华侨代表设宴盛情接待.梅光达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当局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并请转禀清政府:一是要求在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切实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王、余返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建议在悉尼设立中国总领事馆.1909年中国领事馆在墨尔本建立.1912年中国领事馆与澳大利亚政府就5类华人入境问题达成协议.
大多数华人移民都想最终能返回故里,由于语言的障碍,生活方式的差异,移民法的限制以及华人希望回国的愿望,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被同化的很慢.同化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前进,有些华人剪掉辫子,换掉民族服装,穿上尖头皮鞋,系领带,戴西式帽子.1911年以后,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大多是这种澳式打扮.另一种适应方式是华人信奉基督教,这与华人牧师的努力分不开,这种改变也更容易让当地白人接受.信奉基督教后,便采用基督教名,1921年后很多华人采用基督教名.
回忆录
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为了去除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尽量还原历史的本色,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华裔的个人口述史和家族生活回忆录(这些口述中华人都用了教名).因为澳洲的中国人大多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北部,自然这里也就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开始华人移民在金矿区开拓了很多定居点,建立社区.1901年后,金矿的华人社区纷纷解体,悉尼和墨尔本则继续兴旺发达.在墨尔本全州有7349人,其中华人有2200人,聚居在以小伯克街为中心的唐人街.在唐人街中主要是些满足华人需要的进出口商行、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蔬菜水果店、餐饮店、鸦片烟馆和赌场.
南部高原区的很多商铺都位于很小的社区,其中最大的镇子人口不超过5000人,但是中国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忍受着白人的歧视和嘲笑,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卖的东西无所不包,顾客群也渐渐扩大到当地非华人居民和当地出生的华人.口述史和采访记录中有很多对这些当时店铺的描述.
1915年进入洪源百货公司工作的比阿特丽斯还清晰记得店铺的陈设布局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她说:“衣物摆放在长条形的柜台上,鞋子、男式长裤、羊毛开衫、衣服料子杂七杂八得堆在一起,柜台的末端是女式内衣和裙子,柜台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隙留给帽子了.但是我们店里的帽子太多了,现在哪也没有那么多帽子了.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是袜子等零碎东西.钱柜占据店铺的中心.柜台的对面是食品、蔬菜和水果.我们还卖少量家具,不过在另一间屋子里,那里还有五金.”
盖特总是回想他父亲的店铺,20世纪30年代这个商铺在昔日繁荣的锡矿小镇埃玛维尔(Emmaville)开张营业.他说:“我记得幼年时经常在店铺里进进出出,我记得那是两扇门,推开门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梁上挂满商品,我们把单车和浴盆都挂起来卖.我们卖得东西太多了,甚至枪也卖,也卖马蹄铁和马蹄铁钉,还有布料和针头线脑.铺子还有食品区,同时也卖厨房用具.”
贝西的父亲也在埃玛维尔有个铺子,在她的记忆里这个小小的商铺仿佛世外桃源,与20世纪末期的商店相比,那里有着难得的亲和气氛.她说:“在那时候,人们之间亲密诚实,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没有心机和秘密.我们店里时常放着几把椅子,人们在那坐着谈天说地,现在这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华人店主和中国雇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确实与当地人不同,通过悉尼、香港和家乡台山的人际网络(这条人脉网也是他们的商贸网),店主们把亲戚接到新南威尔士.从去国离家的游子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这些位于异乡的商铺就是他们的海外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得到照顾,得以熟悉异国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他们走向独立发展的缓冲区.
店铺中的日常工作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商业和雇佣惯例之上的,店里给刚到澳洲的中国青年或者澳洲出生的华人提供工作和食宿,这些商铺建立在中国家长制和中国式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伊斯特·宋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因弗瑞尔镇的中国商铺做工,他回忆说:“我的工钱是25先令,从始到终我与另外7个中国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另有5个人住在楼上.我们的日程是这样的:7:30的时候厨师敲钟,大家下楼吃饭.我们吃中式早餐吃米粥和中国食品.吃完饭就去店里干活,切切肉等类似的活,一直干到店里开门营业.中午的时候钟声又会响起,所有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去吃饭,午餐一般是英式的.到18点的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这次是中餐.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们要再回到店里干活,做把食糖装袋等类似的工作,一直干到21点左右.”
在格伦因斯镇的光兴商行,老板帕西·杨把一些他认为有劝诫意味的格言,装裱后挂在墙上,比如,如果你现在贫穷也不要怨天尤人,贫穷是因为懒惰.努力工作,不要抱怨困难.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哈维 ·杨总是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生活,他想起那些用来化开蜂蜜的沸水,那些棚屋、马厩,那一缸缸堆满小麦、岩盐、草料的大缸.他还记得:“铺子后来是一小块菜地,鸭子和鸡时常在菜畦间溜达,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盘菜.店里有几个厨师,他们常在后院做面条,新鲜的面条.”
哈维的姐妹还记得中国厨师和其他雇员的食宿状况,她们还记得某些人记得他们住在哪:“乔治· 吴和吉米住在楼上,他们的房间正对着塔特萨尔旅馆,厨师也住在哪,还有个厨师住在靠近厨房的小房间里.铺子后面有个独立的小屋,现在早就被推倒了,那里就是厨房,也是店员们吃饭的地方.”
琳娜·唐也还记得她童年时代的厨师:“我记得小时候有三四个厨师,其中一个光头、块头很大像个巨人,能吃一大碗米饭,名叫乔治·雷的厨师留着长趾甲,我还能想起他在晚上用木棒捣米.”
家乡
这些中国厨子、雇工、食物、语言和其他中国的文化符号,让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超越荒僻的村镇,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建立起剪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因为家庭成员经常回国更加坚固,回国的理由很多,看望亲人,生意需要,或者抱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愿望,落叶归根的意图,或者送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回乡受中国式教育等等.
不过回乡的经历并不总是愉快的,总会有意外的伤害,毕竟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太久,毕竟孩子们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他们惊异得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家乡里的陌生人.很多人都碰到了这种感情上的断层,因弗瑞尔镇上的费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回过香港和内地.乔伊斯·费回忆他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时说:“第一眼看到家乡觉得很奇怪,围着我们跑来跑去的孩子们都没穿鞋,还衣衫不整,我们刚一到那,孩子们就跟着我们”. 乔伊斯的妹妹也说:“我还记得中国孩子朝我们扔石头子,并叫我们白鬼子.”
但回国的经历并不总是让人灰心丧气,很多回忆录上记载说回国像回家一样自在亲切,每次回访都让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纽带更加紧密.而且有时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是比新南威尔士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爱琳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被上海镇住了她说:“上海就像东方的巴黎,一部分是美国化的,一部分是法国式的,那里的建筑精美绝伦,商品无所不包,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很多来过澳大利亚又回国的朋友都住在那.”
然而中国并不安定,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40年代新中国成立,移民运动停止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澳洲联系在一起.以那些早期的店铺作为财富基础,很多澳洲出生的华人得以接受英式教育,之后其他职业也开始向他们敞开.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很多从新南威尔士高原搬到悉尼、布里斯班市等大都市,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人经商有人从政从医.
同时,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开始解冻,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开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二战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一改变.在官方默许种族歧视政策的时候,华裔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当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时候,华裔就会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林梅和她的继女罗萨丽·林的经历和感受就截然不同.
林梅说:“过去,我很小的时候,仅仅因为你是华人,有人就恨你.他们不只是不友好,是从心里恨你.那时候我害怕一个人走路回家,因为他们无缘无故就会把我推倒.”
罗萨丽·林说:“几年前,会说另外的语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但是今天,人们的态度转变了,社会舆论不同了,人们的心胸更加宽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说第二种语言了.”
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化才能共存共荣,才能承认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都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国人对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艰辛并未淡忘.198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在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见到两尊采矿华工铜像,于是填《西江月》一首.词中便有“瞻像俨然神在,长留创业丰碑.浪淘不尽英雄,唤起人间龙种”的佳句.不必说,这是赞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
13个县的移民都讲同一种方言,具有相似的体型、思想和性格,在当地人眼中,华人移民朴素、和蔼、热爱和平、勤奋且节俭,但也有不良嗜好,比如抽鸦片和赌博.他们崇拜偶像,带来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信仰,在金矿区修了很多庙宇.他们的语言、衣着和留的辫子,习惯和癖好,风俗和传统生活方式都同当地人不同.
中国人的出现潜在的威胁到了“白色澳洲”的现实,欧洲白人被中国人的出现和成功吓坏了.“白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华人矿工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的惊恐、怀疑和误解.当时为了调查劳工情况,新南威尔士成立了一个移民调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认为苦力移民会降低白人的生活水平,要求限制移民.
1857年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就写道:“先不考虑中国人带给金矿区的麻风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可怕的病带到哪里——就单单从他们心智低下,身体瘦弱,生活习俗半野蛮化的角度来看,我就反对让他们进入澳洲,他们完全不配融入我们这么文明开化的国家,我要问问大家,他们这些偶像崇拜者能够让我们的基督信仰纯洁吗?这些杏核眼、黄皮肤的东方人能改进我们的种族吗?这些从天朝带来的习性和邪恶能够推动澳大利亚吗?完全不能……”
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念弥漫着整个19世纪晚期,影响着当时的移民立法,1901年澳大利亚移民入国法案就是这种“白色澳大利亚”政策的集中体现,该法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限制非欧洲人来澳大利亚定居.而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对每一个想移民的人强制进行某一种欧洲语言的听写测试,只有特别豁免者除外.豁免证书是经澳大利亚外交部批准,由澳大利亚海关颁发的允许外国人移民澳洲的特别通行证.
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在金矿和锡矿开采殆尽之后,固守落叶归根的中国人很多又回到了祖国,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数急剧下落.尽管危机四伏,也有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扎下了根,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人脉关系,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忍辱负重并且灵活圆滑得面对和处理周围随时出现的敌视.这些定居的中国人,在当地建立家庭,繁衍生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续移民
19世纪50年代发现金矿,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发现锡矿之后,很多华人聚集到新南威尔士的北部高原地区.189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华人占到当地人口的11%,这是华人人数的最高峰,随后锡矿越来越少,很多华人或者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回国,当地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从1891年的1300人下降到1901年的593人,而1921年是169人,到了1947年只有47人了,不过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新人到来了.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赞助亲戚或乡邻移民过来.
在当地华人中,帕西·杨的故事广为流传,足以代表华人移民的努力、辛劳和聪明才智.澳大利亚光兴百货公司(Kwong Sing store)的奠基人帕西·杨1865年出生在广东中山石歧的村庄里,大约20岁的时候通过同村人的关系来到了澳大利亚,随后10年里杨在不同的华人开的店铺打工,生活颠沛流离,10年中的大部分岁月他都在新南威尔士的乡村度过.虽然偶尔也回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在澳洲.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人介绍,帕西·杨来到位于新南威尔士格伦因斯(Glen Innes)地区的光兴商店工作.1907年杨成了光兴的股东之一,到了1912年他几乎接管了光兴,成为了主要的股东和管理者.杨的孩子们相继在澳大利亚出生,他还赞助自己的侄子一个接一个从中国老家来到澳洲他的店铺里工作.不久他的子侄们又一个个的另立门户,开办了自己的店铺,并且相继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帕西·杨家族移民澳洲的活动都发生在1901年移民法实施之后,杨和其他南部高原地区的小业主一样,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让亲戚们陆续来到澳洲,并且想方设法让他们定居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律规定,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并且通过经商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华人可以雇佣中国出生的店员,可以让这些店员暂住一段时期.
伊莱恩·江的父母在滕特菲尔德镇经营商铺,她回忆父母利用人脉关系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亲戚和乡邻服务,这些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进行.他说,“我认为我的父母认识悉尼某些签发移民证的人,他给这些人写信,把某个店铺需要的店员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我父亲把一些人带出来的方法,当然也有别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是主要的.”
一个店铺能雇佣多少中国出生的店员,澳大利亚的法律对此是有规定的,这就刺激华人商店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断扩张,南部高原地区的华人店铺都是如此.因为开办的店铺越多,能够把亲戚带出来的机会就越多.滕特菲尔德镇上的洪源店创立于1899年,到了1915年该店的主要股东和管理者是哈瑞·费,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山石歧的老家度过的,到了30年代,洪源已经在镇上开办了另外3个小商店,在附近村镇有了3个分店和两个零售自助店.
定居华人希望把亲友带出来,为他们的果园、店铺和工厂补充新的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华工,有些人就冒险采取非法的手段,非法移民多由香港商人组织.这些非法移民遭受到难以想象的痛苦.有的人藏在甲板下的货舱、米箱里,整个旅程不见天日,有不少人因窒息而死亡.1905年在悉尼的一艘德国船里发现了23个偷渡客,这些人后来被罚到德属新几内亚做一年苦工.
扎根
华人所采取的谋生方式十分相似,他们主要集中在工业、商业和初级产品生产等领域.多数华人种植蔬菜,菜农本身也是小贩,在清晨5点挑菜到市场,在城市里走街串巷叫卖新鲜蔬菜的华人也很常见.
华人零售店开始营业可以追溯到淘金热,开始主要经营中国货物,大米、丝绸、茶叶、瓷器和生姜等.20世纪前20年中,新南威尔士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牛油、面粉、皮草、金条、铅、煤和木材.出口贸易一半控制在华人手里.1906 年,新南威尔士水果交易所主席断言:香蕉贸易已经从英国人手里转到华人手中.同样的警告不时出现在报纸上.到1921年为止悉尼的许多老牌华人水果商行,永生、泰生、永安都经营香蕉.在墨尔本,添杨、雷鹏和荣享是著名的香蕉和西红柿经销商.华商兴旺发达的例证之一是1917年成立了拥有实际资本10.8万镑的中澳船行,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零售店、食品杂货铺和进出口贸易行都对船行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大多数华人移民与他们的家乡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感情联系.在20世纪前20年中,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的企业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开办起来.这些企业包括制造厂、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以及百货公司.在所有投资和投机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由新南威尔士华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在悉尼的白人公司的帮助下建立,华人创办了三家大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和新安,随后这个商业帝国扩展到远东.过去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是这三家开办的.
华人的成功不可避免的引来白人的不满,澳大利亚作家玛丽·贡特(1861-1942年)在《一个女人在中国》里回忆早年在澳洲的生活经历时说:“我曾多次看到不幸的中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到我父亲家来寻求保护.那些我们称之为流氓的街头恶棍不问情由,任何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往他身上扔石头.”
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还源于经济竞争.以家具制造为例,19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华人靠制作廉价和低档家具谋生,主要制作椅子,货架、脸盆、碗橱和桌子.本土欧洲工匠则垄断了价格高昂的家具.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欧洲人也不得不制造低档产品时,他们发现华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行业.欧洲工匠开始鼓动政府当局,禁止华工移民.他们要求限制华工的劳动时间,并在产品上标明是由白人还是华人制作的,鼓励白人购买白人的商品.面对澳洲同行的打压,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社团,筹措经费游说议员,并聘请律师.1913年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会诞生.
“白澳政策”反而使华人移民变得更团结,更有民族意识.1901年只有少数华人反对移民法,1905年新南威尔士已经召开了州际性质的华人大会商讨共同面对的问题.会议讨论5类华人(商人、官员、传教士、学生和旅游者)入境问题,并为设立中国总领事馆而努力.
劳工阶层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商人少一般都很富裕,并在华人的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上起领导作用,梅光达便是华人中杰出的领导之一.梅光达1850年生于台山市端芬镇山底村龙腾里,9岁时随叔父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拉顿金矿“淘金”.他先是在白人的杂货店里做杂工.因聪明伶俐,被白人金矿主收为养子.1871年,梅光达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1877年养父病逝后继承了养父的产业.之后迁居悉尼,从事商贸活动,专营中国茶叶、丝绸及饮食,很快成为名倾悉尼的华人大富商.1887年5月至8月,清廷派总兵王荣和以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以调查华民商务的名义,到达悉尼、墨尔本等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王、余抵达悉尼时,梅光达亲自率领华侨代表设宴盛情接待.梅光达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当局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并请转禀清政府:一是要求在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切实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王、余返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建议在悉尼设立中国总领事馆.1909年中国领事馆在墨尔本建立.1912年中国领事馆与澳大利亚政府就5类华人入境问题达成协议.
大多数华人移民都想最终能返回故里,由于语言的障碍,生活方式的差异,移民法的限制以及华人希望回国的愿望,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被同化的很慢.同化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前进,有些华人剪掉辫子,换掉民族服装,穿上尖头皮鞋,系领带,戴西式帽子.1911年以后,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大多是这种澳式打扮.另一种适应方式是华人信奉基督教,这与华人牧师的努力分不开,这种改变也更容易让当地白人接受.信奉基督教后,便采用基督教名,1921年后很多华人采用基督教名.
回忆录
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为了去除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尽量还原历史的本色,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华裔的个人口述史和家族生活回忆录(这些口述中华人都用了教名).因为澳洲的中国人大多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北部,自然这里也就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开始华人移民在金矿区开拓了很多定居点,建立社区.1901年后,金矿的华人社区纷纷解体,悉尼和墨尔本则继续兴旺发达.在墨尔本全州有7349人,其中华人有2200人,聚居在以小伯克街为中心的唐人街.在唐人街中主要是些满足华人需要的进出口商行、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蔬菜水果店、餐饮店、鸦片烟馆和赌场.
南部高原区的很多商铺都位于很小的社区,其中最大的镇子人口不超过5000人,但是中国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忍受着白人的歧视和嘲笑,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卖的东西无所不包,顾客群也渐渐扩大到当地非华人居民和当地出生的华人.口述史和采访记录中有很多对这些当时店铺的描述.
1915年进入洪源百货公司工作的比阿特丽斯还清晰记得店铺的陈设布局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她说:“衣物摆放在长条形的柜台上,鞋子、男式长裤、羊毛开衫、衣服料子杂七杂八得堆在一起,柜台的末端是女式内衣和裙子,柜台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隙留给帽子了.但是我们店里的帽子太多了,现在哪也没有那么多帽子了.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是袜子等零碎东西.钱柜占据店铺的中心.柜台的对面是食品、蔬菜和水果.我们还卖少量家具,不过在另一间屋子里,那里还有五金.”
盖特总是回想他父亲的店铺,20世纪30年代这个商铺在昔日繁荣的锡矿小镇埃玛维尔(Emmaville)开张营业.他说:“我记得幼年时经常在店铺里进进出出,我记得那是两扇门,推开门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梁上挂满商品,我们把单车和浴盆都挂起来卖.我们卖得东西太多了,甚至枪也卖,也卖马蹄铁和马蹄铁钉,还有布料和针头线脑.铺子还有食品区,同时也卖厨房用具.”
贝西的父亲也在埃玛维尔有个铺子,在她的记忆里这个小小的商铺仿佛世外桃源,与20世纪末期的商店相比,那里有着难得的亲和气氛.她说:“在那时候,人们之间亲密诚实,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没有心机和秘密.我们店里时常放着几把椅子,人们在那坐着谈天说地,现在这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华人店主和中国雇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确实与当地人不同,通过悉尼、香港和家乡台山的人际网络(这条人脉网也是他们的商贸网),店主们把亲戚接到新南威尔士.从去国离家的游子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这些位于异乡的商铺就是他们的海外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得到照顾,得以熟悉异国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他们走向独立发展的缓冲区.
店铺中的日常工作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商业和雇佣惯例之上的,店里给刚到澳洲的中国青年或者澳洲出生的华人提供工作和食宿,这些商铺建立在中国家长制和中国式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伊斯特·宋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因弗瑞尔镇的中国商铺做工,他回忆说:“我的工钱是25先令,从始到终我与另外7个中国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另有5个人住在楼上.我们的日程是这样的:7:30的时候厨师敲钟,大家下楼吃饭.我们吃中式早餐吃米粥和中国食品.吃完饭就去店里干活,切切肉等类似的活,一直干到店里开门营业.中午的时候钟声又会响起,所有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去吃饭,午餐一般是英式的.到18点的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这次是中餐.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们要再回到店里干活,做把食糖装袋等类似的工作,一直干到21点左右.”
在格伦因斯镇的光兴商行,老板帕西·杨把一些他认为有劝诫意味的格言,装裱后挂在墙上,比如,如果你现在贫穷也不要怨天尤人,贫穷是因为懒惰.努力工作,不要抱怨困难.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哈维 ·杨总是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生活,他想起那些用来化开蜂蜜的沸水,那些棚屋、马厩,那一缸缸堆满小麦、岩盐、草料的大缸.他还记得:“铺子后来是一小块菜地,鸭子和鸡时常在菜畦间溜达,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盘菜.店里有几个厨师,他们常在后院做面条,新鲜的面条.”
哈维的姐妹还记得中国厨师和其他雇员的食宿状况,她们还记得某些人记得他们住在哪:“乔治· 吴和吉米住在楼上,他们的房间正对着塔特萨尔旅馆,厨师也住在哪,还有个厨师住在靠近厨房的小房间里.铺子后面有个独立的小屋,现在早就被推倒了,那里就是厨房,也是店员们吃饭的地方.”
琳娜·唐也还记得她童年时代的厨师:“我记得小时候有三四个厨师,其中一个光头、块头很大像个巨人,能吃一大碗米饭,名叫乔治·雷的厨师留着长趾甲,我还能想起他在晚上用木棒捣米.”
家乡
这些中国厨子、雇工、食物、语言和其他中国的文化符号,让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超越荒僻的村镇,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建立起剪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因为家庭成员经常回国更加坚固,回国的理由很多,看望亲人,生意需要,或者抱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愿望,落叶归根的意图,或者送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回乡受中国式教育等等.
不过回乡的经历并不总是愉快的,总会有意外的伤害,毕竟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太久,毕竟孩子们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他们惊异得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家乡里的陌生人.很多人都碰到了这种感情上的断层,因弗瑞尔镇上的费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回过香港和内地.乔伊斯·费回忆他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时说:“第一眼看到家乡觉得很奇怪,围着我们跑来跑去的孩子们都没穿鞋,还衣衫不整,我们刚一到那,孩子们就跟着我们”. 乔伊斯的妹妹也说:“我还记得中国孩子朝我们扔石头子,并叫我们白鬼子.”
但回国的经历并不总是让人灰心丧气,很多回忆录上记载说回国像回家一样自在亲切,每次回访都让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纽带更加紧密.而且有时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是比新南威尔士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爱琳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被上海镇住了她说:“上海就像东方的巴黎,一部分是美国化的,一部分是法国式的,那里的建筑精美绝伦,商品无所不包,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很多来过澳大利亚又回国的朋友都住在那.”
然而中国并不安定,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40年代新中国成立,移民运动停止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澳洲联系在一起.以那些早期的店铺作为财富基础,很多澳洲出生的华人得以接受英式教育,之后其他职业也开始向他们敞开.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很多从新南威尔士高原搬到悉尼、布里斯班市等大都市,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人经商有人从政从医.
同时,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开始解冻,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开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二战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一改变.在官方默许种族歧视政策的时候,华裔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当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时候,华裔就会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林梅和她的继女罗萨丽·林的经历和感受就截然不同.
林梅说:“过去,我很小的时候,仅仅因为你是华人,有人就恨你.他们不只是不友好,是从心里恨你.那时候我害怕一个人走路回家,因为他们无缘无故就会把我推倒.”
罗萨丽·林说:“几年前,会说另外的语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但是今天,人们的态度转变了,社会舆论不同了,人们的心胸更加宽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说第二种语言了.”
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化才能共存共荣,才能承认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都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国人对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艰辛并未淡忘.198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在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见到两尊采矿华工铜像,于是填《西江月》一首.词中便有“瞻像俨然神在,长留创业丰碑.浪淘不尽英雄,唤起人间龙种”的佳句.不必说,这是赞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