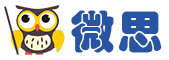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呐喊》中的《一件小事》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⑵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干校六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
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
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
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
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守望的距离》 第一辑 存在之谜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人把哲学当作他的职业,即谋生的手段.另一种人把哲学当作他的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属于前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是“智慧的出卖者”;而苏格拉底自己则堪为后者的典范,他也许是哲学史上因为思想而被定罪并且为了思想而英勇献身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了.
苏格拉底的经历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孔子之于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两人毕生都以教育为主要事业,在哲学思想上都重人生伦理而轻形而上学,分别成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发现,直接用政治的分野来判断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得要领.苏格拉底诚然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期间被处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站在贵族派一边.事实上,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甘冒杀身之祸,独自一人与民众大会或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有比当时奴隶主两派的政治更高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现在,人们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确实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他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文化苦旅》 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 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 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 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杨绛散文》中的《我们仨》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