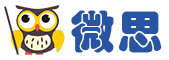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结合艺术作品分析艺术的本质(论文)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内容提要:
本文从敦煌民间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各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境遇、行为方式、大量的爱情描写以及及时记事等四个方面,论述其有关题材范围和主要表现内容.并分析由其混沌多元状态的美学理想导致的主体自觉意识的缺乏,处于不成熟低级层面上的多样化面貌,与缘调切题、铺叙排比的制作方法等三点上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据以总结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萌生初发阶段的文化功用多元取向与实验、创新性质.
《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
考察曲子词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发展历程,如果认为以晚唐温庭筠、韦庄为鼻祖的花间词标志着它的臻达成熟,那么,自隋唐之际的六世纪末叶、七世纪初而直到中唐文宗开成末(840)的约250年间,便属于其始生萌芽阶段.这里主要由民间词与文士词两部分组成,无论质朴率拙、散透出真实生活气息,或清便宛转、多存声诗情韵,都共同显露了奇葩才芳的异常丰采,尽管还轻浅,但是已征兆着那未来的无限辉煌.关于文士词因另有专文论述,[①]故此处只涉及民间词.
一
所谓民间词,系指敦煌写本曲子词,卷中标明的具体抄录时间,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下则于宋至道元年(995);而大体可以考定的制作年代,以后晋开运朝(944—946)的三首〔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边塞苦”为最晚出,不过,基于它们绝大多数作成在盛唐时期,其次是中唐(参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所以并不违背前面的界划.另一方面,抄卷署词作者姓名的仅有温庭筠、欧阳炯等四家六首,其余皆无题名,作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希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而主要属于下层人士,也契合广泛的民间性.当然,上述两端只是外在表象问题,那根本的,在于敦煌词文化功用的多元取向和不规范化的原生态形式,正典型体现着曲子词初生萌发阶段特见的新创、实验、探索性质.下面将就其题材范围、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等进行论析.顺便说明的是,这里所依据的敦煌词集,为最早,也最重要的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伯2838、斯1441),以及周永先《敦煌词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至于任二北后再汇辑《敦煌歌辞总编》,洋洋一千二百余首,举凡写本曲子,乃至属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写本歌辞,诸如大曲、俗曲、佛曲、小调等等,莫不兼收并蓄、包罗无遗,但由于它们过为泛滥,已超轶狭义写本曲子词的范畴,故置而不从.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与后来成熟期的花间、南唐词传统相较,王重民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之条分娄析,归纳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等二十种,诚堪谓大观.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自身内涵的多元指向与复杂性,有些词实际上备载多方面包容,并非仅只单纯的一端,如果过分琐细地区划域轸,难免滋生削足适履、顾此失彼之弊,故而此文参照相关词作的主体取向,大略分类以统括概言之.
对边塞生活的广泛描写,是敦煌曲子词的一大特色.由于迫近玉门关,唐代敦煌向为西北边防重镇,大批驻守军队,常与西域诸族发生战事;另一方面,这儿又是沟连中西亚的交通要冲,胡汉商贾云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以上诸般一并反射到曲子词创作中,自然会形成特定的地域风貌.如《云谣集杂曲子》的开篇之作〔风归云〕《闺怨》二首,所写相思离情是产生在那种具体背景上,有着不同于后来花间传统的意义,因闺中思妇而及长年塞上远征的戍卒,即便待得他荣耀归来,恐怕也是韶华老去、相顾憔悴不堪了.它们反复缠绵,切挚悲苦,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战伐频仍不休,乃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的沉重社会问题,其包容范围自然超迈泛泛习见的男女怨别伤离了.而〔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战偻啰未足多”等篇着重抒写驰逐疆场以建树功业的热情与信心,气概豪迈宏阔,充溢着强烈的尚武精神,与盛唐边塞诗虽有文野精陋之异,然同样体达出大唐帝国蓬勃飞扬、四海一家的辉煌时代消息,制作年代似应相去不远.若考察词中主人公身份,则前篇是位挟怀利器、武艺高强而威猛善战的将军;后者设为问答,显然是联章体,“儒士”凭智谋策计来安邦平定天下,那斩将夺关的勇力便输一筹了——这正反映出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普遍心态.又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记叙吐蕃将领归降李唐王朝的历史事件,虽本意在炫耀中原天国之强盛威赫,但客观上也可见各民族的和解睦融;且主要篇幅是刻画西北游牧民族的独特习俗与生活场景,颇具异域色彩.《旧唐书•吐蕃传》云:“强雄曰选,丈夫曰普,号君长曰赞普”,当知是吐蕃语了.
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描写,这本属曲子词的传统本色题材,故在此际的敦煌词里也占有相当份量,而且它突破单纯闺怨离别的狭隘范围,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显示出其丰富性及作者对这份人类特定情感的深刻理解.如〔拜新月〕“荡子他州去”,除去娓娓描述思妇对远行丈夫的绵绵眷念外,还有对他在外迷花恋柳不忠实行为的怨恨,但是女子只能“自嗟薄命”,最终还期待再相聚而“誓不辜伊”.全词细腻委曲,毕见她的坚贞和软弱,却正缘因没有社会地位、一切都取决于男方喜怒的不幸命运.所以〔抛球乐〕就直面写出被负心抛弃的一位痴情女子的怨悔,相对而言,她比较清醒冷静: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著,淡簿知闻解好么?
结句“淡薄知闻”语该包纳了多少惨痛教训与人生遗憾!或说这是一倡女,不过丝毫未影响词的实质——对真正爱情的渴望追求.那么,〔望江南〕“莫攀我”便代表着这些苦难女性的呼喊,从激愤的反问迸发的心声,一种肯定获取幸福生活权利和恢复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上举诸作多角度地揭示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以及社会给女子造成的伤害.后来《花间集》里亦偶存相类之制,如牛峤〔望江怨〕“东风急”、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等,却是借把玩遣兴眼光发为悬想,缺乏痛切地同情怜惜心,那原来的严肃含义便淡化、消释了.其他再如〔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却又充溢着轻快明媚气氛,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喜剧小镜头,折射出唐代社会风习的开放性,容许异性间比较自由地交往,不像宋以后的礼法束缚日趋严苛.而〔别仙子〕“此时模样”通过男子口吻抒写秋天夜月对远方恋人的怀想,这在同类题材敦煌词中是不多见的,它绵挚深沉,曲曲倾诉衷肠,特见真诚.与之形成艺术对比巨大反差的是〔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它率直奔放,通体燃烧着火样的热烈激情,一如千仞高巅泻落的滔滔大河,往而不复,毫无顾忌,“之死靡矢它”!说词者每将其共汉乐府《上邪》、明俗曲《挂枝儿》“要分离”并论,认为充分展现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至若俞平伯称:“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但山盟海誓皆属“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唐宋词选释》上卷),可备一家言.然而倘如无其他佐证,仅从词作自身考察,似难品出最终“负了心”,故作顿挫之笔的言外意旨.
再者,敦煌词还有许多篇什以各种不同阶层人士的各种不同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为表现题材,显示出广阔的现实人生视野,由之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意义.如古代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无论外出谋生求学归来不易,即或通达平安信息也很困难,所以游子们羁旅天涯的乡思客愁便积郁得格外浓挚,而〔西江月〕“浩渺天涯无际”与〔鹊踏枝〕“独坐更深人寂寂”,或就物景描摹牵引出心思,情景交融互会到以情结景;或是往复呜咽,通篇直抒情愫竟不作一景语,其间的真实感受却并无二致,至若〔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在“莺啼燕语撩乱,争忍不思家”的同样叹喟里,又特地注入“如今时世已参差”的现实因素,最后则归宿为退遁林泉“沉醉卧烟霞”;那么,推想其身份当属失意宦游的士人,而非一般下层民众了.有关这层意思,〔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表述得更加直白坦露,它斥责朝政腐败,“时世掩良贤”,只得采取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并于另外三首同调之作“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亭书满床”、“山后开园种药葵”中,模写高隐之士超脱世俗名利羁绊的淡泊襟怀和随缘自适的田园江湖乐趣,凡此与士大夫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出处进退观念都是一脉相承.又如〔杨柳枝〕由时光流逝而体达到人生倏忽的哲理,浸透着悲凉的生命意识:
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徽尘.
它实质上类同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正是人类缘因社会文明进展到一定高度、自我存在有自觉觉醒时的必然发现;那“只见庭前”云云,更深深契合“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感悟、思考.可以说,对人生本体意义的探索,隋唐一代的诗、词,其旨趣原是相通的.
联章组词〔长相思〕以“作客在江西”领起,分述不同阶层人士“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的各种境遇,作者似乎已饱阅沧桑,老于世故,故能保持一份冷静客观的笔调,其实细味字里行间,仍不失悲天悯人的底蕴,尤其是他关注在人间群体的百态,不再凭以个体的自我作表现中心,应给予特别注意.
最后,是敦煌曲子词的即时、记实性质,直接以时事入调,强调现实功用.这种精神在文人词里一度中断,待到了苏轼,特别是北南宋之交的大变乱时代才又有所恢复,及至南宋而继续强化,形成为一种传统,反过来并影响、改变着词为艳科小道,归旨于遣兴娱宾的另一种主导性传统,推原究始,则是敦煌词已作滥觞了.如〔菩萨蛮〕“千年风争雄异”和〔酒泉子〕“每见惶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引《晚唐书•昭宗纪》,说是为“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避难外逃之事制作,另据尉迟屋《中朝故事》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难,干犯神京,上(昭宗)乃倾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可知二词以叙述笔法表现了晚唐藩镇的又一次祸乱,唯质拙直率,其史料文献价值要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如颂扬敦煌地方首领抵御异族侵掠、安抚各族民众而尽忠唐王室、建立功业的〔望江南〕“曹公德”、“敦煌郡”,一般认为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代事,造语亦不求华藻,然意真字实.像这类性质的词篇还有不少,都并不局囿在个人的得失悲欢,而紧密结合重大社会事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成为敦煌民间词的一种突出创作特色,与《诗•国风》、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可谓息息相通.
二
以上注目于大略要端,分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敦煌写本曲子词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达内容,其余琐屑者便不必一一胪列.下面再进而论析敦煌词呈现的形式特点、审美取向,就其纷繁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总结它含蕴的艺术实质.
首先明显感觉到的,是诗歌传统的重大影响与自我美学理想的混沌多元状态,或者说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些正缘由曲子词萌生初发期的不成熟特殊历史阶段和它的民间文学性质所决定.因为作为一种刚刚出现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还不可能即刻找寻到一套适应自己需要的表现类型、方法,在其不断探索改进、以期逐渐走向完善的漫长历程中,固然会总结新的经验、发现并发展新的规范,但时时回顾传统,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汲取它的营养,特别是相近艺术种类、而又渊源悠远的诗歌,便成为必然的举措.敦煌词主要属于民间制作,作者成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行业,当更易于就一己的耳闻目睹身历事即兴发作咏唱,借助此等流行载体以抒写、传现心声,记叙生活的情貌形态,也契合一般的诗化本质.所以,它的题材内容载具了颇为广泛的人生意义和丰厚的现实性,殊异于后来的文士词——自花间派开启的专力在男女恋情别思的个体心态描摹、指往狭深精细的新的艳科娱人传统,因为敦煌词基本上依然接受着诗的娱己传统.当然,内容与形式原来就是一对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双向制约并进的有机存在物,具体的题材内容必然会选择而且反作用于最适宜其表达的艺术手法;正如上所言,处于原生的不稳定态势中的敦煌词,也很自然地要接受其他文学样式.首先是诗歌传统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不过,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即如民间作品而论,缪远古老的十五国风与汉乐府姑置而不言,便是年代距之较为晚近的南北朝民歌也是春华秋月,风貌迥然各异的;另一方面,词作者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经历、文化素养及艺术偏嗜、水准的差别,当亦不言自明.凡此之类,折射、体达到词上,或趋向雅致清丽,或流于鄙俗不文,恰如王国维评〔天仙子〕诸篇所说:“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里,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二者,是敦煌曲子词原生混沌态的美学理想使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面貌,处在不成熟期的低级层面上,这与后来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鼎盛、深化阶段,词家们自觉地求新创变,打破传统模式而致力于审美的多元取向,显然是有着本质性区分;然而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种低级状态却又拥具了整体上的一致,是为主体风貌、主导倾向的统一化下所包纳的多样,诚如清朱孝臧所概括的:“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疆村丛书:云谣集杂曲子跋》).当然,相当数量的敦煌词,限于民间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水准低下,显得鄙俗粗陋,读来几不终篇,实无可取;但其中的精萃之制,确是质重简咸,明快清新,充溢着特别的初发生命力和天然浑成之致,其境界为文士词藉功力取胜者所不能到.如〔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如〔浣溪沙〕:
一阵风来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瀚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教人肠欲断,况行人.
前者模写女子深夜不得成寐、对月怀想恋人的情景,通体纯出以口语,袒露衷曲无遗;虽不做一毫修饰、不假一丝喻托,却自真挚切实.尤其是结拍两句祝愿,新颖奇妙,而又入情入理,将她那怨、恩、怜、憾的诸般纷乱心绪生动描画出来——实际上一切归源于爱!故于率直发透间,复饶深蕴缠绵情味.后者则写大江上风劲云走、波起浪涌而津头乱舟浮摇之状,运用上下黑白色泽的对映比衬,去突出特定物象“船”的动荡感,由之制造某种惶急不安的气氛,引牵出下阕的问语,最终方才结尾处点明风涛险恶,教“行人”恐惧忧虑的题旨.它先景而后事、情,通篇贯注连接以因果推比,承转自然,似乎毫不费力,其清浅流畅、随口吟出,极具民谣船歌风味,并让人联想到李白《横江词》:“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的意象境界,浓重感受到相互间的类通处.
三者,是缘调切题的制作方式和铺叙排比的表现手法,因为敦煌曲子词属于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初创阶段的产物,民间作者探索、尝试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还是比较拘谨的,难以完全放手,随心适意地处理两者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一般而言,值创调之后,其曲调名便当然地具备对内容的规定、指向作用,使词中描写、反映的情景事物契合调名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调名兼有乐曲与题目的双重性,如同诗歌的题目一样.如〔别仙子〕咏离别愁怨、〔赞浦子〕咏蕃将、〔天仙子〕咏女子憎爱分明思、〔破阵子〕咏从军壮志、〔内空娇〕咏美女形态容貌、〔献忠(表)心〕咏翊载皇室、〔酒泉子〕咏边塞战事、〔谒金门〕咏隐士出山朝帝、〔定风波〕咏平息战乱安定天下,等等不一而足,正显示了词调初行时的特别普遍现象.类似风气延续及晚唐西蜀的《花间集》,缘由年代相距未远,故而仍得流传维持,虽然势头已曾次减弱;待到了宋,古风顿失,曲调名与词中所叙写者大率无涉,它除却标志声律音乐的固有规范外,不再拥具其他意义,而词家往往于调名下另出题目,来说明此篇的旨趣内容.这种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曲子词的发展、丰富而趋于成熟的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和后来文士词专注在心绪意态的抒发、偏重内向深层的创作主流不同,敦煌词多为缘事生发,故每假以情因事出或情隐事间的结构命思,又由其事常属为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习经历见者,一旦通过铺叙排比的手法表现出来,也就觉得亲切生动,别显新鲜活泼.如〔南歌子〕二首:
斜倚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
蝉鬓朱帘乱,金钗旧殿分.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这是联章体,特用对话的形式出之,配合紧密而一一仔细铺陈,推究其原来或许存在着某种故事背景,是以词中明显表示出具体的情节性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指明了.倘若仅就眼前的词句看,上一首男方咄咄气势逼人,必欲盘根察底;后一首女子委宛诉述,言挚情切,二人的神态举止皆历历可以揣摩见,极像一幅形象逼真的画卷、一场活动紧凑的独幕剧,“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②].有人据〔南歌子〕的形式特征推测说:“此二词当时可能入歌舞戏,入陆参军,入俗讲,佐以说白,或其他辞体,以供讲唱”[③],实在很有见地,又如〔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此篇主旨在描叙闺中思妇怨别念远的情怀,但却不作一正面摹写抒发语,也不去刻画其心境形态,而别从灵鹊报喜的古老民间传说立意,通过上下阕的女主角与鹊儿话语间接展示出来,构想、手法新颖奇特,妙趣忽生天外.它已不再只限于简单的拟人化,而颇见故事意味,即景促发,笔致流动,用了质实朴直的口语俗语,洋溢着浓郁真切的日常生活气息.至于〔鱼歌子〕《月》:“绣帘前,美人睡,庭前 子频频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帏出屏韩,整云髻,莺啼湿尽相思泪共别人,好说我不是,你莫辜天负地”,写男子的浮薄轻狂和女子的抱怨责备,言外以见她的真挚情意,却是借助一个细节式生活小场面体现,这种模式对后来的文士词有所影响,如花间派的张泼、欧阳炯都有类近的仿效之制,只不过更为精整绮华罢了.另外,本篇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结拍是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但“莺啼湿尽相思泪”却十分风雅,真可置之花间、南唐词语里,并无愧色,就总体言,它在敦煌词中显得较工丽,或许是经过了文士的润饰.
最后,还必须顺便说明的,是唐圭璋曾归纳敦煌词的写作特点为七条:“一、有衬字,二、有和声,三、有双调,四、字数不定,五、平仄不拘,六、叶韵不定,七“咏题名”(《敦煌词校释》),后来吴熊和在此基础上更为参酌取舍,重又提出六条之说:“一、有衬字,二、字数不定,三、平仄不拘,四、叶韵不定,五、咏调名本意者多,六、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并且总结说:“敦煌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合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和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④]所论颇为详明精当,若与晚唐五代以后进展到成熟阶段的规范化了的曲子词相参较比照,便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晰.不过,这里所论列的,除却“咏题名”、“咏调名本意者多”一条以外,大都偏重于从体式、格律、韵调等纯形式角度着眼,似当属外在的量化把握方式了,容易作出较精确切凿的“实性”判断;若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有关表现内容,题材范围,以及艺术手法、审美意趣等内在质类的观照途径,尝试为趋向宽泛灵活的“虚性”感受,那么,最后的总体结论,就有可能更为深刻全面.
注释:
①乔力《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张璋、黄番《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唐宋词通论》,参见第169—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文从敦煌民间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各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境遇、行为方式、大量的爱情描写以及及时记事等四个方面,论述其有关题材范围和主要表现内容.并分析由其混沌多元状态的美学理想导致的主体自觉意识的缺乏,处于不成熟低级层面上的多样化面貌,与缘调切题、铺叙排比的制作方法等三点上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据以总结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萌生初发阶段的文化功用多元取向与实验、创新性质.
《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
考察曲子词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发展历程,如果认为以晚唐温庭筠、韦庄为鼻祖的花间词标志着它的臻达成熟,那么,自隋唐之际的六世纪末叶、七世纪初而直到中唐文宗开成末(840)的约250年间,便属于其始生萌芽阶段.这里主要由民间词与文士词两部分组成,无论质朴率拙、散透出真实生活气息,或清便宛转、多存声诗情韵,都共同显露了奇葩才芳的异常丰采,尽管还轻浅,但是已征兆着那未来的无限辉煌.关于文士词因另有专文论述,[①]故此处只涉及民间词.
一
所谓民间词,系指敦煌写本曲子词,卷中标明的具体抄录时间,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下则于宋至道元年(995);而大体可以考定的制作年代,以后晋开运朝(944—946)的三首〔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边塞苦”为最晚出,不过,基于它们绝大多数作成在盛唐时期,其次是中唐(参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所以并不违背前面的界划.另一方面,抄卷署词作者姓名的仅有温庭筠、欧阳炯等四家六首,其余皆无题名,作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希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而主要属于下层人士,也契合广泛的民间性.当然,上述两端只是外在表象问题,那根本的,在于敦煌词文化功用的多元取向和不规范化的原生态形式,正典型体现着曲子词初生萌发阶段特见的新创、实验、探索性质.下面将就其题材范围、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等进行论析.顺便说明的是,这里所依据的敦煌词集,为最早,也最重要的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伯2838、斯1441),以及周永先《敦煌词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至于任二北后再汇辑《敦煌歌辞总编》,洋洋一千二百余首,举凡写本曲子,乃至属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写本歌辞,诸如大曲、俗曲、佛曲、小调等等,莫不兼收并蓄、包罗无遗,但由于它们过为泛滥,已超轶狭义写本曲子词的范畴,故置而不从.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与后来成熟期的花间、南唐词传统相较,王重民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之条分娄析,归纳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等二十种,诚堪谓大观.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自身内涵的多元指向与复杂性,有些词实际上备载多方面包容,并非仅只单纯的一端,如果过分琐细地区划域轸,难免滋生削足适履、顾此失彼之弊,故而此文参照相关词作的主体取向,大略分类以统括概言之.
对边塞生活的广泛描写,是敦煌曲子词的一大特色.由于迫近玉门关,唐代敦煌向为西北边防重镇,大批驻守军队,常与西域诸族发生战事;另一方面,这儿又是沟连中西亚的交通要冲,胡汉商贾云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以上诸般一并反射到曲子词创作中,自然会形成特定的地域风貌.如《云谣集杂曲子》的开篇之作〔风归云〕《闺怨》二首,所写相思离情是产生在那种具体背景上,有着不同于后来花间传统的意义,因闺中思妇而及长年塞上远征的戍卒,即便待得他荣耀归来,恐怕也是韶华老去、相顾憔悴不堪了.它们反复缠绵,切挚悲苦,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战伐频仍不休,乃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的沉重社会问题,其包容范围自然超迈泛泛习见的男女怨别伤离了.而〔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战偻啰未足多”等篇着重抒写驰逐疆场以建树功业的热情与信心,气概豪迈宏阔,充溢着强烈的尚武精神,与盛唐边塞诗虽有文野精陋之异,然同样体达出大唐帝国蓬勃飞扬、四海一家的辉煌时代消息,制作年代似应相去不远.若考察词中主人公身份,则前篇是位挟怀利器、武艺高强而威猛善战的将军;后者设为问答,显然是联章体,“儒士”凭智谋策计来安邦平定天下,那斩将夺关的勇力便输一筹了——这正反映出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普遍心态.又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记叙吐蕃将领归降李唐王朝的历史事件,虽本意在炫耀中原天国之强盛威赫,但客观上也可见各民族的和解睦融;且主要篇幅是刻画西北游牧民族的独特习俗与生活场景,颇具异域色彩.《旧唐书•吐蕃传》云:“强雄曰选,丈夫曰普,号君长曰赞普”,当知是吐蕃语了.
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描写,这本属曲子词的传统本色题材,故在此际的敦煌词里也占有相当份量,而且它突破单纯闺怨离别的狭隘范围,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显示出其丰富性及作者对这份人类特定情感的深刻理解.如〔拜新月〕“荡子他州去”,除去娓娓描述思妇对远行丈夫的绵绵眷念外,还有对他在外迷花恋柳不忠实行为的怨恨,但是女子只能“自嗟薄命”,最终还期待再相聚而“誓不辜伊”.全词细腻委曲,毕见她的坚贞和软弱,却正缘因没有社会地位、一切都取决于男方喜怒的不幸命运.所以〔抛球乐〕就直面写出被负心抛弃的一位痴情女子的怨悔,相对而言,她比较清醒冷静: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著,淡簿知闻解好么?
结句“淡薄知闻”语该包纳了多少惨痛教训与人生遗憾!或说这是一倡女,不过丝毫未影响词的实质——对真正爱情的渴望追求.那么,〔望江南〕“莫攀我”便代表着这些苦难女性的呼喊,从激愤的反问迸发的心声,一种肯定获取幸福生活权利和恢复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上举诸作多角度地揭示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以及社会给女子造成的伤害.后来《花间集》里亦偶存相类之制,如牛峤〔望江怨〕“东风急”、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等,却是借把玩遣兴眼光发为悬想,缺乏痛切地同情怜惜心,那原来的严肃含义便淡化、消释了.其他再如〔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却又充溢着轻快明媚气氛,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喜剧小镜头,折射出唐代社会风习的开放性,容许异性间比较自由地交往,不像宋以后的礼法束缚日趋严苛.而〔别仙子〕“此时模样”通过男子口吻抒写秋天夜月对远方恋人的怀想,这在同类题材敦煌词中是不多见的,它绵挚深沉,曲曲倾诉衷肠,特见真诚.与之形成艺术对比巨大反差的是〔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它率直奔放,通体燃烧着火样的热烈激情,一如千仞高巅泻落的滔滔大河,往而不复,毫无顾忌,“之死靡矢它”!说词者每将其共汉乐府《上邪》、明俗曲《挂枝儿》“要分离”并论,认为充分展现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至若俞平伯称:“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但山盟海誓皆属“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唐宋词选释》上卷),可备一家言.然而倘如无其他佐证,仅从词作自身考察,似难品出最终“负了心”,故作顿挫之笔的言外意旨.
再者,敦煌词还有许多篇什以各种不同阶层人士的各种不同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为表现题材,显示出广阔的现实人生视野,由之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意义.如古代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无论外出谋生求学归来不易,即或通达平安信息也很困难,所以游子们羁旅天涯的乡思客愁便积郁得格外浓挚,而〔西江月〕“浩渺天涯无际”与〔鹊踏枝〕“独坐更深人寂寂”,或就物景描摹牵引出心思,情景交融互会到以情结景;或是往复呜咽,通篇直抒情愫竟不作一景语,其间的真实感受却并无二致,至若〔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在“莺啼燕语撩乱,争忍不思家”的同样叹喟里,又特地注入“如今时世已参差”的现实因素,最后则归宿为退遁林泉“沉醉卧烟霞”;那么,推想其身份当属失意宦游的士人,而非一般下层民众了.有关这层意思,〔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表述得更加直白坦露,它斥责朝政腐败,“时世掩良贤”,只得采取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并于另外三首同调之作“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亭书满床”、“山后开园种药葵”中,模写高隐之士超脱世俗名利羁绊的淡泊襟怀和随缘自适的田园江湖乐趣,凡此与士大夫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出处进退观念都是一脉相承.又如〔杨柳枝〕由时光流逝而体达到人生倏忽的哲理,浸透着悲凉的生命意识:
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徽尘.
它实质上类同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正是人类缘因社会文明进展到一定高度、自我存在有自觉觉醒时的必然发现;那“只见庭前”云云,更深深契合“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感悟、思考.可以说,对人生本体意义的探索,隋唐一代的诗、词,其旨趣原是相通的.
联章组词〔长相思〕以“作客在江西”领起,分述不同阶层人士“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的各种境遇,作者似乎已饱阅沧桑,老于世故,故能保持一份冷静客观的笔调,其实细味字里行间,仍不失悲天悯人的底蕴,尤其是他关注在人间群体的百态,不再凭以个体的自我作表现中心,应给予特别注意.
最后,是敦煌曲子词的即时、记实性质,直接以时事入调,强调现实功用.这种精神在文人词里一度中断,待到了苏轼,特别是北南宋之交的大变乱时代才又有所恢复,及至南宋而继续强化,形成为一种传统,反过来并影响、改变着词为艳科小道,归旨于遣兴娱宾的另一种主导性传统,推原究始,则是敦煌词已作滥觞了.如〔菩萨蛮〕“千年风争雄异”和〔酒泉子〕“每见惶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引《晚唐书•昭宗纪》,说是为“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避难外逃之事制作,另据尉迟屋《中朝故事》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难,干犯神京,上(昭宗)乃倾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可知二词以叙述笔法表现了晚唐藩镇的又一次祸乱,唯质拙直率,其史料文献价值要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如颂扬敦煌地方首领抵御异族侵掠、安抚各族民众而尽忠唐王室、建立功业的〔望江南〕“曹公德”、“敦煌郡”,一般认为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代事,造语亦不求华藻,然意真字实.像这类性质的词篇还有不少,都并不局囿在个人的得失悲欢,而紧密结合重大社会事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成为敦煌民间词的一种突出创作特色,与《诗•国风》、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可谓息息相通.
二
以上注目于大略要端,分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敦煌写本曲子词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达内容,其余琐屑者便不必一一胪列.下面再进而论析敦煌词呈现的形式特点、审美取向,就其纷繁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总结它含蕴的艺术实质.
首先明显感觉到的,是诗歌传统的重大影响与自我美学理想的混沌多元状态,或者说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些正缘由曲子词萌生初发期的不成熟特殊历史阶段和它的民间文学性质所决定.因为作为一种刚刚出现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还不可能即刻找寻到一套适应自己需要的表现类型、方法,在其不断探索改进、以期逐渐走向完善的漫长历程中,固然会总结新的经验、发现并发展新的规范,但时时回顾传统,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汲取它的营养,特别是相近艺术种类、而又渊源悠远的诗歌,便成为必然的举措.敦煌词主要属于民间制作,作者成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行业,当更易于就一己的耳闻目睹身历事即兴发作咏唱,借助此等流行载体以抒写、传现心声,记叙生活的情貌形态,也契合一般的诗化本质.所以,它的题材内容载具了颇为广泛的人生意义和丰厚的现实性,殊异于后来的文士词——自花间派开启的专力在男女恋情别思的个体心态描摹、指往狭深精细的新的艳科娱人传统,因为敦煌词基本上依然接受着诗的娱己传统.当然,内容与形式原来就是一对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双向制约并进的有机存在物,具体的题材内容必然会选择而且反作用于最适宜其表达的艺术手法;正如上所言,处于原生的不稳定态势中的敦煌词,也很自然地要接受其他文学样式.首先是诗歌传统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不过,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即如民间作品而论,缪远古老的十五国风与汉乐府姑置而不言,便是年代距之较为晚近的南北朝民歌也是春华秋月,风貌迥然各异的;另一方面,词作者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经历、文化素养及艺术偏嗜、水准的差别,当亦不言自明.凡此之类,折射、体达到词上,或趋向雅致清丽,或流于鄙俗不文,恰如王国维评〔天仙子〕诸篇所说:“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里,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二者,是敦煌曲子词原生混沌态的美学理想使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面貌,处在不成熟期的低级层面上,这与后来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鼎盛、深化阶段,词家们自觉地求新创变,打破传统模式而致力于审美的多元取向,显然是有着本质性区分;然而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种低级状态却又拥具了整体上的一致,是为主体风貌、主导倾向的统一化下所包纳的多样,诚如清朱孝臧所概括的:“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疆村丛书:云谣集杂曲子跋》).当然,相当数量的敦煌词,限于民间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水准低下,显得鄙俗粗陋,读来几不终篇,实无可取;但其中的精萃之制,确是质重简咸,明快清新,充溢着特别的初发生命力和天然浑成之致,其境界为文士词藉功力取胜者所不能到.如〔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如〔浣溪沙〕:
一阵风来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瀚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教人肠欲断,况行人.
前者模写女子深夜不得成寐、对月怀想恋人的情景,通体纯出以口语,袒露衷曲无遗;虽不做一毫修饰、不假一丝喻托,却自真挚切实.尤其是结拍两句祝愿,新颖奇妙,而又入情入理,将她那怨、恩、怜、憾的诸般纷乱心绪生动描画出来——实际上一切归源于爱!故于率直发透间,复饶深蕴缠绵情味.后者则写大江上风劲云走、波起浪涌而津头乱舟浮摇之状,运用上下黑白色泽的对映比衬,去突出特定物象“船”的动荡感,由之制造某种惶急不安的气氛,引牵出下阕的问语,最终方才结尾处点明风涛险恶,教“行人”恐惧忧虑的题旨.它先景而后事、情,通篇贯注连接以因果推比,承转自然,似乎毫不费力,其清浅流畅、随口吟出,极具民谣船歌风味,并让人联想到李白《横江词》:“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的意象境界,浓重感受到相互间的类通处.
三者,是缘调切题的制作方式和铺叙排比的表现手法,因为敦煌曲子词属于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初创阶段的产物,民间作者探索、尝试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还是比较拘谨的,难以完全放手,随心适意地处理两者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一般而言,值创调之后,其曲调名便当然地具备对内容的规定、指向作用,使词中描写、反映的情景事物契合调名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调名兼有乐曲与题目的双重性,如同诗歌的题目一样.如〔别仙子〕咏离别愁怨、〔赞浦子〕咏蕃将、〔天仙子〕咏女子憎爱分明思、〔破阵子〕咏从军壮志、〔内空娇〕咏美女形态容貌、〔献忠(表)心〕咏翊载皇室、〔酒泉子〕咏边塞战事、〔谒金门〕咏隐士出山朝帝、〔定风波〕咏平息战乱安定天下,等等不一而足,正显示了词调初行时的特别普遍现象.类似风气延续及晚唐西蜀的《花间集》,缘由年代相距未远,故而仍得流传维持,虽然势头已曾次减弱;待到了宋,古风顿失,曲调名与词中所叙写者大率无涉,它除却标志声律音乐的固有规范外,不再拥具其他意义,而词家往往于调名下另出题目,来说明此篇的旨趣内容.这种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曲子词的发展、丰富而趋于成熟的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和后来文士词专注在心绪意态的抒发、偏重内向深层的创作主流不同,敦煌词多为缘事生发,故每假以情因事出或情隐事间的结构命思,又由其事常属为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习经历见者,一旦通过铺叙排比的手法表现出来,也就觉得亲切生动,别显新鲜活泼.如〔南歌子〕二首:
斜倚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
蝉鬓朱帘乱,金钗旧殿分.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这是联章体,特用对话的形式出之,配合紧密而一一仔细铺陈,推究其原来或许存在着某种故事背景,是以词中明显表示出具体的情节性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指明了.倘若仅就眼前的词句看,上一首男方咄咄气势逼人,必欲盘根察底;后一首女子委宛诉述,言挚情切,二人的神态举止皆历历可以揣摩见,极像一幅形象逼真的画卷、一场活动紧凑的独幕剧,“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②].有人据〔南歌子〕的形式特征推测说:“此二词当时可能入歌舞戏,入陆参军,入俗讲,佐以说白,或其他辞体,以供讲唱”[③],实在很有见地,又如〔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此篇主旨在描叙闺中思妇怨别念远的情怀,但却不作一正面摹写抒发语,也不去刻画其心境形态,而别从灵鹊报喜的古老民间传说立意,通过上下阕的女主角与鹊儿话语间接展示出来,构想、手法新颖奇特,妙趣忽生天外.它已不再只限于简单的拟人化,而颇见故事意味,即景促发,笔致流动,用了质实朴直的口语俗语,洋溢着浓郁真切的日常生活气息.至于〔鱼歌子〕《月》:“绣帘前,美人睡,庭前 子频频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帏出屏韩,整云髻,莺啼湿尽相思泪共别人,好说我不是,你莫辜天负地”,写男子的浮薄轻狂和女子的抱怨责备,言外以见她的真挚情意,却是借助一个细节式生活小场面体现,这种模式对后来的文士词有所影响,如花间派的张泼、欧阳炯都有类近的仿效之制,只不过更为精整绮华罢了.另外,本篇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结拍是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但“莺啼湿尽相思泪”却十分风雅,真可置之花间、南唐词语里,并无愧色,就总体言,它在敦煌词中显得较工丽,或许是经过了文士的润饰.
最后,还必须顺便说明的,是唐圭璋曾归纳敦煌词的写作特点为七条:“一、有衬字,二、有和声,三、有双调,四、字数不定,五、平仄不拘,六、叶韵不定,七“咏题名”(《敦煌词校释》),后来吴熊和在此基础上更为参酌取舍,重又提出六条之说:“一、有衬字,二、字数不定,三、平仄不拘,四、叶韵不定,五、咏调名本意者多,六、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并且总结说:“敦煌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合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和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④]所论颇为详明精当,若与晚唐五代以后进展到成熟阶段的规范化了的曲子词相参较比照,便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晰.不过,这里所论列的,除却“咏题名”、“咏调名本意者多”一条以外,大都偏重于从体式、格律、韵调等纯形式角度着眼,似当属外在的量化把握方式了,容易作出较精确切凿的“实性”判断;若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有关表现内容,题材范围,以及艺术手法、审美意趣等内在质类的观照途径,尝试为趋向宽泛灵活的“虚性”感受,那么,最后的总体结论,就有可能更为深刻全面.
注释:
①乔力《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③张璋、黄番《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唐宋词通论》,参见第169—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