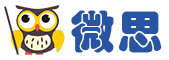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古代谁批判过儒家思想,主要事件,和主要观点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吴虞对儒家封建礼教的评判
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觉醒.一大批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并以之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谱写了一曲悲壮雄伟、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本文试就五四时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公元1872—1949年)对儒家思想的基本态度这一微观的侧面,再现那一时代的精神风貌.
一、对儒家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
及对“新文化”的倡导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天地宇宙间存在着一种超然的人格力量,宇宙之运作规则,社会之更替嬗变,乃至人生之吉凶祸福,皆受制于超然的人格力量.吴虞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是这种流行观念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指出,在儒家思想看来,凡是“天下之治乱,帝王之传授,强弱之相役,斯文之兴丧,人事之是非,遭遇之通塞,子孙之贤愚,门徒之生死,疾病之愈否,心性之存养,无一不归之于天,天之权威”.《吴虞文续录·荀子之天论与辟NFDB4祥》卷下.在这种观念中,“天”是不可预测的超然力量,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人对自身的命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吴虞强调说,儒家思想在其发端之始便与宿命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吴虞还对儒家思想政治化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定于一尊,长达数千年,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儒家思想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吴虞指出:一方面,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构成要素之一就是承认尊卑贵贱、上下等级的合理性,换言之,就是承认“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阶级有种种之区别”.《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竭力维持各等级间的协调稳定,儒家的这种社会理想模式与统治者的治国治民目标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对君主专制政体推崇备至,“直驾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为君主所凭藉所利用”,《吴虞文续录·读荀子书后》卷下.所以,儒家思想在其长期演变过程中,始终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紧密配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五四时期,抨击儒教,为一时之风尚,但抨击儒教的目的是什么,则理解各不相同.吴虞认为,我们抨击儒教,目的就是批判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性,具体说来就是,儒家在其政治化过程中,阻碍科学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严重束缚中国国民的思想,极度摧残中国国民的心灵……,完全丧失了其合理的思想因素和生命活力,因此,对这种危及社会与民生的学说,我们必须予以批判.但是,吴虞不同意那种把儒教与孔子本人混为一谈的做法.他认为,抨击儒教,不必涉及孔子本人人格之高下问题,就是说,“孔子与孔教(即儒教)从根本性质而言是两回事,从道德人格上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他还援引日本久保天随的话说:“孔子伟大而多面……故与希腊之大圣梭(苏)格拉底相同,其生活道德之模范也”《吴虞文续录·经疑》卷上.,可见,吴虞对孔子的人格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故而,吴虞在其儒家批判意识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原则:即其批判对象,不是孔子,而是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造成极大危害的孔教.
儒家学说极重社会伦常关系,把修身养性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和“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基于这一思想特征,儒家把“孝”摆在突出地位,孔子就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吴虞对这一现象看得很清楚,他评价儒家说:“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儒家所谓“孝”,乃一切伦常之本,所有后天萌生的七情六欲皆源于其中.吴虞把儒家所提倡之“孝”与儒家之“礼”做了一番比较,指出它们在儒家道德哲学结构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他认为,“孝”是更内在的东西,它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孝”具有内具而非外附,自觉而非强加的特点;而“礼”相对于“孝”,是外在的规定,其“作用全在保护尊贵长上,使一般人民安于卑贱幼下、恭恭顺顺的”《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孝”与“礼”相为表里,“礼”只是“孝”的内在逻辑展开.吴虞抨击道,由于儒家重孝重礼,人的自由天性和日常行为受到很大限定.下面我们将看到,吴虞很多措辞激烈的思想观点都是从这种思想引发出来的.
吴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道德——政治领域.正如前面所说,他认为儒家之“孝”要通过“礼”来体现,因此,他对“礼”的本质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吴虞指出,“礼”不是笼统的,“礼”有礼教、礼仪之分别,“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他认为,礼仪是社会存在必须的一些仪式,“不论文明野蛮人都是有的”《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而礼教则不同,它是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僵化凝固化,使之成为空洞无物的道德说教.更有甚者,儒家还不断为这些道德说教寻找理论和现实依据.吴虞适应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对儒家的这种学说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把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他认为,儒家赋予道德以神秘色彩,掩盖了道德的真实本质,吴虞对这种被人为歪曲了的道德现象进行了世俗还原.他明确指出,所谓道德,根本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捉摸的,而是在人自身及群体关系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就是说“道德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道德作为历史范畴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属性.吴虞对先秦道、儒、法诸家的道德伦理观作了横向比较,他指出,在儒家肆意弘扬道德并以之作为人生行为准则的时代,道家则把道德视为社会沦丧、人性泯灭的根由.在道家看来,“道德是不道德的原因”,“所谓道德,不过是媚于世俗多数人的一个东西”《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道家认为道德是违背人性的,它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若要使社会机体稳定和睦,人之本性返朴归真,必须抛弃虚假道德而代之以自然无为.法家则以一种发展进化的眼光审视道德,认为“社会的变迁,道德的进步,都是因时制宜,没有一定的规则”《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法家把道德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发展了,道德原则也随之改变.这种以进化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与儒家那种“以一定不变为神圣”的道德原则是针锋相对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目的在于区别是非优劣.吴虞在比较过程中,批判了儒家的道德不变论,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起源论观点.吴虞指出:“原来道德本是社会的意志,即由多数压制的所发现”《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还指出:“道德是人为的”.把吴虞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我们就可看出,他所说的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谓“人为”,不是孤立的“人为”,而是社会的“人为”,社会内部不同之“人”各为其所“为”,构成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需要用道德关系来调节.基于这种发展的观点,吴虞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已不再适合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那么中国应有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吴虞像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热切期望着在中华大地上能出现一种崭新的道德关系,他指出,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中国社会必须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运动,以造就新的国民素质;与此同时,还必须扩大知识视野,虚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博采兼攻,虚襟研究”,这样,我们中华民族“虽不敢与欧美颉颃,其与俄之大彼得,日之明治或堪匹敌”《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吴虞非常重视知识经验的积累,有着“广从世界求知识”《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的宏伟抱负,他本人就对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有深入的研究.吴虞强调指出,积累知识是确立新的道德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现今需要的知识预备充足,有了充足的知识,再去讲道德不迟.若知识尚且不够,便去讲道德,便去争新旧,那就蠢得可怜、糟得可怜了”《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人们只要掌握了现代文化知识,就有了鉴赏分辨的能力,也就不会被那些旧的陈腐的伦理道德所欺骗了.吴虞坚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大通、人群进化”的变革时代,中国在专制时期形成的那套社会习惯、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等,应统统予以荡涤打破,“采取世界最通行、最合人生的习惯来改正从前荒谬、愚陋、残酷、野蛮的‘土人习惯’、‘土人道德’”《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这头睡狮才有觉醒的希望,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由此可见,吴虞是“五四”时期坚定的反儒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儒家那套旧礼教旧道德是违背人性、阻碍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腐朽之物.吴虞还认为,“革新”是摆脱儒家思想桎梏的唯一途径.他之所谓“革新”,不是指儒教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和结构更新,而是指依靠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来取代它.这种“革新”主张与吴虞提倡的“博采兼攻,虚襟研究”,“广从世界求知识”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吴虞认为,革新是思想进步的巨大推动力,西方社会由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由于培根、笛卡尔创立了新学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新思想新学说,然而,由于“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吴虞文录·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二者相比之下,是非优劣一目了然.吴虞深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中国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最根本问题就是必须彻底抛弃儒家思想,消除封建等级制度及诸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然后在中国成立“共和制度”与“君民共主”制度.吴虞的愿望是,在中国,如果“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儒家思想之消除,将何以取代之?吴虞明确指出,将以西方基督教思想取而代之.在当时,曾有人对他说:“孔教既不足法,信仰耶稣亦足为道德之标准”《吴虞日记·1913年4月18日》上册.,吴虞深表同意.其后,吴虞这种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形成一种坚强的信念,他说:“邪(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传布浸久,风俗人心皆受其影响,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竟著之于宪法,而罔敢或渝矣”《吴虞文录·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把西方耶稣教看作“平等自由博爱”的崇高象征,西方社会正是产生了耶稣教,才“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吴虞在耶稣教与西方社会发展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的逻辑联系.他还认为,耶稣教主张废除社会不平等,恢复人的自由本性及拯救人类受苦受难的心灵,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公平合理,因而耶稣教是“真理”,“亦最有价值”.
吴虞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新旧思想大冲突的时代,观察问题难免带有片面性.可以说,吴虞对西方耶稣教的评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用它来取代中国的儒教更显得难以实行.他未能透过“自由博爱”的虚伪辞藻洞观西方社会的本质问题,因而不能正确把握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的耶稣教的精蕴.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突出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人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决心.吴虞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唤醒中国的民众,引导民众把目光从狭小的民族意识圈子里解脱出来,破除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旧礼教旧道德,适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起了发聋振聩的推动作用.
二、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
同构学说的剖判 吴虞对传统的旧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抨击,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同构学说也做了细致入微的剖判.他明确提出,儒家家—国同质同构的核心点即在于忠孝,忠孝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力量,其直接作用就表现在它促成了家—国同质同构体系的最终形成.
众所周知,家庭是一个社会机体构成的细胞单位,正如人体的细胞构成不同于人体本身一样,家庭在构成、形态、功能上也与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下,由于忠孝的联接,这两种原属不同形态的存在实体呈现出一种趋同倾向,质言之就是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单位——家庭基本上丧失了其作为家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与个性特质,其形态表现为:家庭是国家机能的缩小,国家是家庭机能的扩大,家、国以某种奇特的组合方式构筑成稳固的实体,共同履行着治理国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职责.对这种社会现象,吴虞评价说:“儒家以孝弟(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他还指出:“儒家……往往把君父二人并称,忠孝二字连用,忠孝二字,就是拿来连接专制朝廷和专制家庭的一个秘诀”《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忠孝的观念对维系一个民族的稳定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吴虞指出,在儒家思想看来,作为国家之臣民,居家则孝敬父母兄长,有此孝之情感,出则自然将此情感移至君主,这种放大了的情感便是忠.吴虞强调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与“国家”是同一个意思,忠君即是忠国.君父至高无上,是真理的代表,权力的化身.在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吴虞文续录·松冈小史序》.,其结果导致了“家与国无分”,“君与父无异”《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的奇异的社会现象.
对于儒家奉若至宝的“忠孝”二字,吴虞沉重地感叹道,在国家与家族双重枷锁钳制下,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天真无邪的生命被残酷无情的忠孝二字所吞噬所扼杀;有多少奋起抗争的时代叛逆者最终成为忠孝的殉葬品,又有多少企图冲破忠孝桎梏的尝试者最终被杀人无血的忠孝所湮没.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不惟如此,吴虞还指出,儒家提倡忠孝之社会目的就是强化家—国结构,“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文录·说孝》卷上.正是由于忠孝观念的长期影响以及以之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家—国同质同构的社会联合体,酿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拘守徘徊于宗法社会中而难以自拔的困境.吴虞这样说:“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庭制度为之梗也”,他还说:“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吴虞的结论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不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社会形态,忠孝思想观念以及家—国同质同构体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吴虞还指出,要使中国传统的思想形态出现重大转折,除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外,就是努力促使家—国同质同构体的分化,以恢复家、国各自的社会功能.要达到这一目的,吴虞认为首先必须破除忠孝观念在社会各领域的消极影响,吴虞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无“孝”则“忠”无所依附,由“孝”所构筑的家族制度既解,那么由“忠”所维系的君主制度也随之而散.他说:“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吴虞在主张对儒家思想及家—国结构体的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视精神性力量,他以为消除了忠孝观念,家—国结构体便自然瓦解,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精神性的东西是社会、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意识到一种精神的变更有赖于整个经济基础的改变及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但是,对吴虞这种主精神力量的倾向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精神的力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精神力量的参与,历史将成为无主体无生命的空壳.然而,在考察精神的作用问题时,我们应将精神的决定作用和精神的影响作用区别开来,细究吴虞思想之义,似乎将两者没有分别,给人以精神决定论的感觉.吴虞意识到精神、思想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反馈能力和调节功能,并认为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左右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往我们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往往把对精神、观念性因素蹬强调称之为历史唯心论,殊不知,往往正是由于这种强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奥秘,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全部人类的发展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儒教毒化国民、摧残人性的深刻反省
可以这么说,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面反省是五四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思想(实指儒家思想)的弊端之一就是毒化国民,摧残人性,吴虞也持这种态度.吴虞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做了一番刻画.他指出,中国人自育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竟沾沾自喜而不自觉,于是乎,整个民族陷入“乐天知命,委天任运之见解,沉浸于数千年中国之人心而莫能自拔”《吴虞文续录·荀子之天论与辟NFDB4祥》卷下.的悲惨境地.吴虞悲愤地感叹道:吾国自来由六经之理论制成礼法,由礼法之实行而为习俗,风俗既成,则人由之,而不知积非成是,虽已酿成亡国之祸亦不一悟”《吴虞文续录·国立四川大学文本科同学录序》卷下.,“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吴虞文录·说孝》卷上.然而,吴虞又痛心而愤慨地指出:世世代代惨遭封建礼教束缚、蹂躏乃至心灵枯死、肉体麻木的中国国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罹遭礼教迫害之不幸,并没有从一种人性自觉的角度对这种吃人礼教进行抗争,以维护人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当然少数反叛者是有的,但终归于惨败),更没有对产生这种异化社会现象和人格扭曲现象的社会制度予以全面自觉的反省.这不正是中国国民性历史悲剧之所在么!吴虞指出,国民虽愚昧若此,然那些自命清高的道德腐儒们却置社会职责于不顾,崇尚“空泛道德之谈,惝恍性命之理,沾沾于汉宗,切切于陆王,自以为命世大贤”《吴虞文录·消极革命之达》.,其所作为,无助于人生,无益于社会,直到“辽金元清之侵入”,“日本来占据他桑梓的地方”,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这些人不是起而抗争,誓死报国,而只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终于“举祖宗之国而弃之,而皆甘为这臣仆也”《吴虞文续录·国立成都大学文预科同学录序》卷下.对这种怯懦的民族性一面,吴虞感慨系之,他说,千百年来,中国国民“毕生颠倒于专制之圣贤、经传、帝王威势之下,而认为当然之正义、沉沦于阶级之制度,奴隶之生活,不敢妄想脱其羁绊,殊可悲也!”《吴虞文录·驳康有为君主之论不可废说》卷下.吴虞还指出,封建时代中国之国民性如此愚陋保守,视封建伦理纲常为金科玉律,在思想深层必导致夜郎自大、盲目排斥的抵触心理.吴虞认为,儒家便具有这种封闭、排外的思想倾向,在儒家看来,“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卷下.,长期以来,儒家正统的“息邪说,辟异端”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国民的意识之中,其威力之大,韧性之强,具有同化任何外来事物的能力,于是乎,人人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而对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又鄙夷轻蔑而闭塞之,使不能传布”《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卷下.这种守旧心理正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虞还认为,礼教的禁锢束缚使人丧失了自我.对此,吴虞援引汉顺帝对臣子樊英说的话:“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吴虞文续录·荀子之政治论》卷下.,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微贱、何等渺小!一个人的命运又是何等地无法预卜和把握.吴虞还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以习惯为法律、以道德代法律的倾向,并指出了它们的吃人本性.在中国古代,只要君主说某人有罪当诛,就等于在法律上做出了判决,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的体现,臣民的生命对君主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甚至连草芥都不如.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其地位更为卑下,痛苦更为深重,“二千年来受儒教之毒,压抑束缚,蔽聪塞明,无学问,无能力”吴曾兰:《女权平议》.,全然成为男性的附庸,生儿育女的工具.吴虞举例说,唐将臧洪,杀死爱妾以享兵将,“把人当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然而,就是“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准他为‘壮烈’,国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正是这些恶魔为了“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吴虞最后痛切地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真是惨酷极了!”《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讲到这里,吴虞得出结论说,礼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礼教,这是吴虞继戴震、鲁迅等人的反封建礼教思想而对中国封建礼教所进行的又一次猛烈抨击.吴虞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呼唤着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确立.面对封建专制社会“人民无独立之自由”,“子女无独立之人格”《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的社会现实,吴虞向全社会发出了挑战宣言,他宣称,现在是人民自由、人格独立的时候了,让那一些压抑人性、亵渎人格的旧礼教见鬼去吧!他庄严地宣布:“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吴虞热切地期望:在当今中国,必须学会尊重人及人格,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也应有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人们在父母面前,也“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因为“同为人类,同做人民,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吴虞文录·说孝》卷上.,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正是度过了漫长的非人之路,所以更加充满了对人之路的憧憬和向往.
吴虞对中国国民性的刻画及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既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人文思潮的强烈影响,又与整个五四时期社会发展的一般思想进程相吻合.吴虞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他是五四时期激烈的非儒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当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所说:“现代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多,但是像吴氏那么热诚来呼号非儒论的一个也没有”《吴虞文录·吴虞底儒教破坏说》.可见,吴虞是全身心投入到“非儒”的斗争中的,这从时人对他的评论中(“只手打孔家店”),也可略窥一斑.
历史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然而历史需要我们去反思.吴虞对儒家思想的评判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是撷取了其中几个方面.他的反封建反礼教意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的时代,在中西思想文化再次面临大撞击大沟通的时代,把握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从微观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先进思想和先驱者,无疑是有意义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30 11:20
《文心雕龙》里的儒家思想批判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充满儒家思想的文学理论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它的思想作用以及文学价值都有待探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性地位无需多言,而书中所阐发那一个个经典论断充满着儒家思想,表现在他对孔子言行和文章的极度推崇,对“诗教”传统和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强调等方面.在新时代眼光的审视下,《文心雕龙》里的儒家思想有着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如过分尊古、过度强调道德作用等等,本文将从这几点展开批评.
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觉醒.一大批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思想文化,并以之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谱写了一曲悲壮雄伟、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本文试就五四时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公元1872—1949年)对儒家思想的基本态度这一微观的侧面,再现那一时代的精神风貌.
一、对儒家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
及对“新文化”的倡导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天地宇宙间存在着一种超然的人格力量,宇宙之运作规则,社会之更替嬗变,乃至人生之吉凶祸福,皆受制于超然的人格力量.吴虞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是这种流行观念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指出,在儒家思想看来,凡是“天下之治乱,帝王之传授,强弱之相役,斯文之兴丧,人事之是非,遭遇之通塞,子孙之贤愚,门徒之生死,疾病之愈否,心性之存养,无一不归之于天,天之权威”.《吴虞文续录·荀子之天论与辟NFDB4祥》卷下.在这种观念中,“天”是不可预测的超然力量,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人对自身的命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吴虞强调说,儒家思想在其发端之始便与宿命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吴虞还对儒家思想政治化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定于一尊,长达数千年,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儒家思想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吴虞指出:一方面,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构成要素之一就是承认尊卑贵贱、上下等级的合理性,换言之,就是承认“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阶级有种种之区别”.《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竭力维持各等级间的协调稳定,儒家的这种社会理想模式与统治者的治国治民目标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对君主专制政体推崇备至,“直驾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为君主所凭藉所利用”,《吴虞文续录·读荀子书后》卷下.所以,儒家思想在其长期演变过程中,始终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紧密配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五四时期,抨击儒教,为一时之风尚,但抨击儒教的目的是什么,则理解各不相同.吴虞认为,我们抨击儒教,目的就是批判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性,具体说来就是,儒家在其政治化过程中,阻碍科学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严重束缚中国国民的思想,极度摧残中国国民的心灵……,完全丧失了其合理的思想因素和生命活力,因此,对这种危及社会与民生的学说,我们必须予以批判.但是,吴虞不同意那种把儒教与孔子本人混为一谈的做法.他认为,抨击儒教,不必涉及孔子本人人格之高下问题,就是说,“孔子与孔教(即儒教)从根本性质而言是两回事,从道德人格上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他还援引日本久保天随的话说:“孔子伟大而多面……故与希腊之大圣梭(苏)格拉底相同,其生活道德之模范也”《吴虞文续录·经疑》卷上.,可见,吴虞对孔子的人格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故而,吴虞在其儒家批判意识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原则:即其批判对象,不是孔子,而是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造成极大危害的孔教.
儒家学说极重社会伦常关系,把修身养性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和“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基于这一思想特征,儒家把“孝”摆在突出地位,孔子就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吴虞对这一现象看得很清楚,他评价儒家说:“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儒家所谓“孝”,乃一切伦常之本,所有后天萌生的七情六欲皆源于其中.吴虞把儒家所提倡之“孝”与儒家之“礼”做了一番比较,指出它们在儒家道德哲学结构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他认为,“孝”是更内在的东西,它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孝”具有内具而非外附,自觉而非强加的特点;而“礼”相对于“孝”,是外在的规定,其“作用全在保护尊贵长上,使一般人民安于卑贱幼下、恭恭顺顺的”《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孝”与“礼”相为表里,“礼”只是“孝”的内在逻辑展开.吴虞抨击道,由于儒家重孝重礼,人的自由天性和日常行为受到很大限定.下面我们将看到,吴虞很多措辞激烈的思想观点都是从这种思想引发出来的.
吴虞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道德——政治领域.正如前面所说,他认为儒家之“孝”要通过“礼”来体现,因此,他对“礼”的本质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吴虞指出,“礼”不是笼统的,“礼”有礼教、礼仪之分别,“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他认为,礼仪是社会存在必须的一些仪式,“不论文明野蛮人都是有的”《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而礼教则不同,它是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僵化凝固化,使之成为空洞无物的道德说教.更有甚者,儒家还不断为这些道德说教寻找理论和现实依据.吴虞适应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对儒家的这种学说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把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他认为,儒家赋予道德以神秘色彩,掩盖了道德的真实本质,吴虞对这种被人为歪曲了的道德现象进行了世俗还原.他明确指出,所谓道德,根本不是什么神秘不可捉摸的,而是在人自身及群体关系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就是说“道德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道德作为历史范畴具有不可避免的阶级属性.吴虞对先秦道、儒、法诸家的道德伦理观作了横向比较,他指出,在儒家肆意弘扬道德并以之作为人生行为准则的时代,道家则把道德视为社会沦丧、人性泯灭的根由.在道家看来,“道德是不道德的原因”,“所谓道德,不过是媚于世俗多数人的一个东西”《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道家认为道德是违背人性的,它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若要使社会机体稳定和睦,人之本性返朴归真,必须抛弃虚假道德而代之以自然无为.法家则以一种发展进化的眼光审视道德,认为“社会的变迁,道德的进步,都是因时制宜,没有一定的规则”《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法家把道德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发展了,道德原则也随之改变.这种以进化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与儒家那种“以一定不变为神圣”的道德原则是针锋相对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目的在于区别是非优劣.吴虞在比较过程中,批判了儒家的道德不变论,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起源论观点.吴虞指出:“原来道德本是社会的意志,即由多数压制的所发现”《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还指出:“道德是人为的”.把吴虞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我们就可看出,他所说的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谓“人为”,不是孤立的“人为”,而是社会的“人为”,社会内部不同之“人”各为其所“为”,构成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需要用道德关系来调节.基于这种发展的观点,吴虞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已不再适合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那么中国应有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吴虞像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热切期望着在中华大地上能出现一种崭新的道德关系,他指出,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中国社会必须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运动,以造就新的国民素质;与此同时,还必须扩大知识视野,虚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博采兼攻,虚襟研究”,这样,我们中华民族“虽不敢与欧美颉颃,其与俄之大彼得,日之明治或堪匹敌”《吴虞文续录·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卷上.吴虞非常重视知识经验的积累,有着“广从世界求知识”《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的宏伟抱负,他本人就对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有深入的研究.吴虞强调指出,积累知识是确立新的道德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现今需要的知识预备充足,有了充足的知识,再去讲道德不迟.若知识尚且不够,便去讲道德,便去争新旧,那就蠢得可怜、糟得可怜了”《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人们只要掌握了现代文化知识,就有了鉴赏分辨的能力,也就不会被那些旧的陈腐的伦理道德所欺骗了.吴虞坚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大通、人群进化”的变革时代,中国在专制时期形成的那套社会习惯、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等,应统统予以荡涤打破,“采取世界最通行、最合人生的习惯来改正从前荒谬、愚陋、残酷、野蛮的‘土人习惯’、‘土人道德’”《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论》.,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这头睡狮才有觉醒的希望,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由此可见,吴虞是“五四”时期坚定的反儒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儒家那套旧礼教旧道德是违背人性、阻碍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腐朽之物.吴虞还认为,“革新”是摆脱儒家思想桎梏的唯一途径.他之所谓“革新”,不是指儒教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和结构更新,而是指依靠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来取代它.这种“革新”主张与吴虞提倡的“博采兼攻,虚襟研究”,“广从世界求知识”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吴虞认为,革新是思想进步的巨大推动力,西方社会由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由于培根、笛卡尔创立了新学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新思想新学说,然而,由于“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吴虞文录·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二者相比之下,是非优劣一目了然.吴虞深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以之为指导思想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中国要富强、民族要振兴,最根本问题就是必须彻底抛弃儒家思想,消除封建等级制度及诸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然后在中国成立“共和制度”与“君民共主”制度.吴虞的愿望是,在中国,如果“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儒家思想之消除,将何以取代之?吴虞明确指出,将以西方基督教思想取而代之.在当时,曾有人对他说:“孔教既不足法,信仰耶稣亦足为道德之标准”《吴虞日记·1913年4月18日》上册.,吴虞深表同意.其后,吴虞这种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形成一种坚强的信念,他说:“邪(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传布浸久,风俗人心皆受其影响,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竟著之于宪法,而罔敢或渝矣”《吴虞文录·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把西方耶稣教看作“平等自由博爱”的崇高象征,西方社会正是产生了耶稣教,才“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吴虞在耶稣教与西方社会发展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的逻辑联系.他还认为,耶稣教主张废除社会不平等,恢复人的自由本性及拯救人类受苦受难的心灵,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公平合理,因而耶稣教是“真理”,“亦最有价值”.
吴虞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新旧思想大冲突的时代,观察问题难免带有片面性.可以说,吴虞对西方耶稣教的评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用它来取代中国的儒教更显得难以实行.他未能透过“自由博爱”的虚伪辞藻洞观西方社会的本质问题,因而不能正确把握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的耶稣教的精蕴.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主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突出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人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决心.吴虞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唤醒中国的民众,引导民众把目光从狭小的民族意识圈子里解脱出来,破除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旧礼教旧道德,适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起了发聋振聩的推动作用.
二、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
同构学说的剖判 吴虞对传统的旧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抨击,对儒家的家庭—国家同质同构学说也做了细致入微的剖判.他明确提出,儒家家—国同质同构的核心点即在于忠孝,忠孝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力量,其直接作用就表现在它促成了家—国同质同构体系的最终形成.
众所周知,家庭是一个社会机体构成的细胞单位,正如人体的细胞构成不同于人体本身一样,家庭在构成、形态、功能上也与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下,由于忠孝的联接,这两种原属不同形态的存在实体呈现出一种趋同倾向,质言之就是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单位——家庭基本上丧失了其作为家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与个性特质,其形态表现为:家庭是国家机能的缩小,国家是家庭机能的扩大,家、国以某种奇特的组合方式构筑成稳固的实体,共同履行着治理国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职责.对这种社会现象,吴虞评价说:“儒家以孝弟(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他还指出:“儒家……往往把君父二人并称,忠孝二字连用,忠孝二字,就是拿来连接专制朝廷和专制家庭的一个秘诀”《吴虞文录·墨子的劳农主义》卷下.,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忠孝的观念对维系一个民族的稳定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吴虞指出,在儒家思想看来,作为国家之臣民,居家则孝敬父母兄长,有此孝之情感,出则自然将此情感移至君主,这种放大了的情感便是忠.吴虞强调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与“国家”是同一个意思,忠君即是忠国.君父至高无上,是真理的代表,权力的化身.在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吴虞文续录·松冈小史序》.,其结果导致了“家与国无分”,“君与父无异”《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的奇异的社会现象.
对于儒家奉若至宝的“忠孝”二字,吴虞沉重地感叹道,在国家与家族双重枷锁钳制下,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天真无邪的生命被残酷无情的忠孝二字所吞噬所扼杀;有多少奋起抗争的时代叛逆者最终成为忠孝的殉葬品,又有多少企图冲破忠孝桎梏的尝试者最终被杀人无血的忠孝所湮没.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不惟如此,吴虞还指出,儒家提倡忠孝之社会目的就是强化家—国结构,“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文录·说孝》卷上.正是由于忠孝观念的长期影响以及以之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家—国同质同构的社会联合体,酿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拘守徘徊于宗法社会中而难以自拔的困境.吴虞这样说:“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庭制度为之梗也”,他还说:“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吴虞的结论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不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社会形态,忠孝思想观念以及家—国同质同构体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吴虞还指出,要使中国传统的思想形态出现重大转折,除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外,就是努力促使家—国同质同构体的分化,以恢复家、国各自的社会功能.要达到这一目的,吴虞认为首先必须破除忠孝观念在社会各领域的消极影响,吴虞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无“孝”则“忠”无所依附,由“孝”所构筑的家族制度既解,那么由“忠”所维系的君主制度也随之而散.他说:“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吴虞文录·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卷上.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吴虞在主张对儒家思想及家—国结构体的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视精神性力量,他以为消除了忠孝观念,家—国结构体便自然瓦解,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精神性的东西是社会、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意识到一种精神的变更有赖于整个经济基础的改变及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但是,对吴虞这种主精神力量的倾向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精神的力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精神力量的参与,历史将成为无主体无生命的空壳.然而,在考察精神的作用问题时,我们应将精神的决定作用和精神的影响作用区别开来,细究吴虞思想之义,似乎将两者没有分别,给人以精神决定论的感觉.吴虞意识到精神、思想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反馈能力和调节功能,并认为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左右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往我们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往往把对精神、观念性因素蹬强调称之为历史唯心论,殊不知,往往正是由于这种强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奥秘,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全部人类的发展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儒教毒化国民、摧残人性的深刻反省
可以这么说,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面反省是五四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思想(实指儒家思想)的弊端之一就是毒化国民,摧残人性,吴虞也持这种态度.吴虞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做了一番刻画.他指出,中国人自育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竟沾沾自喜而不自觉,于是乎,整个民族陷入“乐天知命,委天任运之见解,沉浸于数千年中国之人心而莫能自拔”《吴虞文续录·荀子之天论与辟NFDB4祥》卷下.的悲惨境地.吴虞悲愤地感叹道:吾国自来由六经之理论制成礼法,由礼法之实行而为习俗,风俗既成,则人由之,而不知积非成是,虽已酿成亡国之祸亦不一悟”《吴虞文续录·国立四川大学文本科同学录序》卷下.,“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吴虞文录·说孝》卷上.然而,吴虞又痛心而愤慨地指出:世世代代惨遭封建礼教束缚、蹂躏乃至心灵枯死、肉体麻木的中国国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罹遭礼教迫害之不幸,并没有从一种人性自觉的角度对这种吃人礼教进行抗争,以维护人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当然少数反叛者是有的,但终归于惨败),更没有对产生这种异化社会现象和人格扭曲现象的社会制度予以全面自觉的反省.这不正是中国国民性历史悲剧之所在么!吴虞指出,国民虽愚昧若此,然那些自命清高的道德腐儒们却置社会职责于不顾,崇尚“空泛道德之谈,惝恍性命之理,沾沾于汉宗,切切于陆王,自以为命世大贤”《吴虞文录·消极革命之达》.,其所作为,无助于人生,无益于社会,直到“辽金元清之侵入”,“日本来占据他桑梓的地方”,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这些人不是起而抗争,誓死报国,而只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终于“举祖宗之国而弃之,而皆甘为这臣仆也”《吴虞文续录·国立成都大学文预科同学录序》卷下.对这种怯懦的民族性一面,吴虞感慨系之,他说,千百年来,中国国民“毕生颠倒于专制之圣贤、经传、帝王威势之下,而认为当然之正义、沉沦于阶级之制度,奴隶之生活,不敢妄想脱其羁绊,殊可悲也!”《吴虞文录·驳康有为君主之论不可废说》卷下.吴虞还指出,封建时代中国之国民性如此愚陋保守,视封建伦理纲常为金科玉律,在思想深层必导致夜郎自大、盲目排斥的抵触心理.吴虞认为,儒家便具有这种封闭、排外的思想倾向,在儒家看来,“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卷下.,长期以来,儒家正统的“息邪说,辟异端”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国民的意识之中,其威力之大,韧性之强,具有同化任何外来事物的能力,于是乎,人人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而对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又鄙夷轻蔑而闭塞之,使不能传布”《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卷下.这种守旧心理正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虞还认为,礼教的禁锢束缚使人丧失了自我.对此,吴虞援引汉顺帝对臣子樊英说的话:“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吴虞文续录·荀子之政治论》卷下.,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微贱、何等渺小!一个人的命运又是何等地无法预卜和把握.吴虞还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以习惯为法律、以道德代法律的倾向,并指出了它们的吃人本性.在中国古代,只要君主说某人有罪当诛,就等于在法律上做出了判决,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的体现,臣民的生命对君主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甚至连草芥都不如.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其地位更为卑下,痛苦更为深重,“二千年来受儒教之毒,压抑束缚,蔽聪塞明,无学问,无能力”吴曾兰:《女权平议》.,全然成为男性的附庸,生儿育女的工具.吴虞举例说,唐将臧洪,杀死爱妾以享兵将,“把人当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然而,就是“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准他为‘壮烈’,国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正是这些恶魔为了“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吴虞最后痛切地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真是惨酷极了!”《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讲到这里,吴虞得出结论说,礼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礼教,这是吴虞继戴震、鲁迅等人的反封建礼教思想而对中国封建礼教所进行的又一次猛烈抨击.吴虞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呼唤着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确立.面对封建专制社会“人民无独立之自由”,“子女无独立之人格”《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的社会现实,吴虞向全社会发出了挑战宣言,他宣称,现在是人民自由、人格独立的时候了,让那一些压抑人性、亵渎人格的旧礼教见鬼去吧!他庄严地宣布:“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吴虞文录·吃人与礼教》.吴虞热切地期望:在当今中国,必须学会尊重人及人格,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也应有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人们在父母面前,也“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因为“同为人类,同做人民,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吴虞文录·说孝》卷上.,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正是度过了漫长的非人之路,所以更加充满了对人之路的憧憬和向往.
吴虞对中国国民性的刻画及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既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人文思潮的强烈影响,又与整个五四时期社会发展的一般思想进程相吻合.吴虞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他是五四时期激烈的非儒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当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所说:“现代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多,但是像吴氏那么热诚来呼号非儒论的一个也没有”《吴虞文录·吴虞底儒教破坏说》.可见,吴虞是全身心投入到“非儒”的斗争中的,这从时人对他的评论中(“只手打孔家店”),也可略窥一斑.
历史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然而历史需要我们去反思.吴虞对儒家思想的评判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是撷取了其中几个方面.他的反封建反礼教意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的时代,在中西思想文化再次面临大撞击大沟通的时代,把握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从微观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先进思想和先驱者,无疑是有意义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30 11:20
《文心雕龙》里的儒家思想批判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充满儒家思想的文学理论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它的思想作用以及文学价值都有待探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性地位无需多言,而书中所阐发那一个个经典论断充满着儒家思想,表现在他对孔子言行和文章的极度推崇,对“诗教”传统和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强调等方面.在新时代眼光的审视下,《文心雕龙》里的儒家思想有着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如过分尊古、过度强调道德作用等等,本文将从这几点展开批评.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