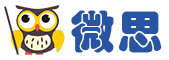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给我几篇很好的很优美的散文
最好能给我多一些题目.
最好能给我多一些题目.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人间草木•槐花
汪曾祺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自得耀眼.来了放蜂人.蜂箱都放好了,他
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
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
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
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
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
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
容不迫,慢条斯理的.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
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
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
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
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
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
服,买鞋,买饼干.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
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
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大,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
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
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选自《人间草木》)
一朵午荷 洛夫
这是去夏九月问的旧事,我们为了荷花与爱情的关系,曾发生过一次温和的争辩.“爱荷的人不但爱它花的娇美,叶的清香,枝的挺秀,也爱它夏天的喧哗,爱它秋季的寥落,甚至觉得连喂养它的那池污泥也污得有些道理.”
“花凋了呢?”
“爱它的翠叶田田.”“叶残了呢?”
“听打在上面的雨声呀!”
“这种结论岂不太过罗曼蒂克.”“你认为……?”
“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
记得那是一个落着小雨的下午,午睡醒来,突然想到去博物馆参观一位朋友的画展.为了喜欢那份凉意,手里的伞一直未曾撑开,冷雨溜进颈子里,竟会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喜.沿着南海路走过去,一辆红色计程车侧身驰过,溅了我一裤脚的泥水.抵达画廊时,正在口袋里乱掏,你突然在我面前出现,并递过来一块雪白的手帕.老是喜欢做一些平淡而又惊人的事,我心想.
这时,室外的雨势越来越大,群马奔腾,众鼓齐擂,整个世界茏罩在一阵阵激越的杀伐声中,但极度的喧嚣中又有着出奇的静.我们相偕跨进了面对植物园的阳台.“快过来看!”你靠着玻璃窗失神地叫着.我挨过去向窗外一瞧,顿时为窗下一幅自然的奇景所感动,怔住.窗下是一大片池荷,荷花多已凋谢,或者说多已雕塑成一个个结实的莲蓬.满池的青叶在雨中翻飞着,大者如鼓,小者如掌,雨粒劈头劈脸洒将下来,鼓声与掌声响成一片,节奏急迫而多变化,声势相当慑人.
我们印象中的荷一向是青叶如盖,俗气一点说是亭亭玉立,之所以亭亭,是因为它有那一把瘦长的腰身,风中款摆,韵致绝佳.但在雨中,荷是一群仰着脸的动物,专注而矜持,显得格外英姿勃发,矫健中另有一种娇媚.雨落在它们的脸上,开始水珠沿着中心滴溜溜地转,渐渐凝聚成一个水晶球,越向叶子的边沿扩展,水晶球也越旋越大,瘦弱的枝杆似乎已支持不住水球的重负,由旋转而左摇右晃,惊险万分.我们的眼睛越
睁越大,心跳加速,紧紧抓住窗棂的手掌沁出了汗水.猝然,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荷身一侧,哗啦一声,整个叶面上的水球倾泻而下,紧接着荷枝弹身而起,又恢复了原有的挺拔和矜持,我们也随之嘘了一口气.我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一片浓烟刚好将脸上尚未褪尽的红晕掩住.
也许由于过度紧张,也许由于天气阴郁,这天下午我除了在思索你那句“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的话外,一直到画廊关门,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
但我真正懂得荷,是在今年一个秋末的下午.这次我是诚心去植物园看荷的,心里有了准备,仍不免有些紧张.跨进园门,在石凳上坐憩一下,调整好呼吸后,再轻步向荷池走去.
噫!那些荷花呢?怎么又碰上花残季节,在等我的只剩下满池涌动的青叶,好大一拳的空虚向我袭来.花是没了,取代的只是几株枯干的莲蓬,黑黑瘦瘦,一副营养不良的身架,跟丰腴的荷叶对照之下,显得越发孤绝.这时突然想起我那首《众荷喧哗》中的诗句:“众荷喧哗/而你是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柔的一朵/……”
午后的园子很静,除了我别无游客.我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满池的青荷出神.众荷田田亭亭如故,但歌声已歇,盛况不再.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繁华与喧嚣,到处拥挤不堪;现在静下来了,剩下我独自坐在这里,抽烟,扔石子,看池中自己的倒影碎了,又拼合起来,情势逆转,现在已轮到残荷来欣赏我的孤寂了.想到这里,我竞有些赧然,甚至感到难堪起来.其实,孤寂也并不就是一种羞耻,
当有人在欣赏我的孤寂时,我绝不会认为他有任何罪过.朋友,这点你不要跟我辩,兴衰无非都是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今年花事已残,明年照样由根而茎而叶而花,仍然一大朵一大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接受人的赞赏与攀折,它却毫无顾忌地一脚踩污泥,一掌擎蓝天,激红着脸大声唱着“我是一朵盛开的莲”,唱完后不到几天,它又安静地退回到叶残花凋的自然运转过程中去接受另一次安排,等到第二年再来接唱.
扑扑尘土,站起身来,绕着荷池走了一圈,绕第二圈时,突然发现眼前红影一闪而没.我又回来绕了半匝,然后蹲下身子搜寻,在重重叠叠的荷叶掩盖中,终于找到了一朵将谢而未谢,却已冷寂无声的红莲,我惊喜得手足无措起来,这不正是去夏那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柔的一朵吗?
(选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读本②?一朵午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有删节)
春风
林斤澜
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粱,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撤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臂腿,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
麦苗在霜冰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大毂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先自1980年4月8日《北京晚报》)
饮一口汨罗江
熊召政
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的诗史中,已经流了,两千多年.诗人如我辈,视之为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取它一瓢饮者,更是大有人在.当然,饮的不是玉液琼浆,而是在漫长的春秋中浊了又清,清了又浊的苦涩.这苦涩,比秋茶更酽.
这会儿,我正在汨罗江的岸边,掬起一杯浑黄得叫人失望的江水.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我可是千里奔驰特意赶来的啊!
脖子一扬,我,饮了一口汨罗.
立刻,我感觉到,就像有一条吐着芯子的蛇窜入我的喉管,冰凉而滑溜,在我肝胆心肺间穿行,如同在烟雨迷蒙的天气里穿过三峡的蛟龙.
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脸色难堪,埋怨说:“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这水太脏了.”我报以苦笑.
朋友继续说:“你们诗人都是疯子,不过,也像圣徒.恒河的水污染那么严重,圣徒们也是长途跋涉,非得跑到那里去喝一口.”
我得承认,朋友这么说,并不是讥笑我,他只是不理解.我的行囊中,带有青岛啤酒和可口可乐,为什么,我非得饮这浑黄的汨罗?
这小小的隔阂,让我想起禅家的一段公案.一次,著名禅师药山椎俨看到一个和尚,问:“你从哪里来?”和尚答:“我从湖南来.”药山又问:“湖水是不是在泛滥?”答:“湖水还没有泛滥.”药山接着说:“奇怪,下那么多雨,湖水为什么没有泛滥?”和尚对此没有满意的回答.因而药山的弟子云岩说:“是在泛滥.”同时,药山另一个弟子东山大叫道:“何劫中不曾泛滥!”细细品味这句话,不得不佩服禅家独特的思维品质.何水不脏?我想对朋友当头棒喝的这四个字,本源于何劫中不曾泛滥的追问.
不过,那四个字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然而由禅家推及诗家,我想得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滥,每个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节的湖水泛滥,又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呢?屈原淹死在汨罗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汨罗不只是湘北的这一条,也不尽然是由波涛组成,知道这一点的,恐怕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滥!还可以推补一句,何处没有汨罗江?
嵇康的汨罗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广陵散》;李白的汨罗江,是一片明月;苏东坡的汨罗江,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贬谪之骆;秋瑾的汨罗江,是一把砍头的大刀;闻一多的汨罗江,是一颗穿胸的子弹……到这里,我禁不住问自己:
你的汨罗江会是什么呢?
据考证,屈原本姓熊,是我的同宗.从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写诗做人的坐标.每当灾难来临,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汨罗江.好多次,当我的愤怒无法宣泄,我就想跑到这里来,跳进去,让汨罗再汨罗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这汨罗江的岸边,饮了一口浑黄后,我的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
江面上,二三渔舟以一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悠然,从我眼前飘过.不知道屈原为何许人也的渔翁,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五月的阳光.偶尔有几条鱼苗,看上去像二月的柳叶,也被渔翁扔进了鱼篓.那也是他的收获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渔翁之意,却是肯定在于鱼的.
中国的渔翁形象,从劝屈原“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惯看秋月春风”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权力更迭,人间兴废,与他们毫不相干.船头上一坐,就着明月,两三条小鱼,一壶酒,他们活的好逍遥啊!你看这条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汨罗江上,屈原早就不见了,而渔翁仍在.
这就是我的惆怅所在.一位清代的湖南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
萧瑟寒塘垂竹枝,长桥屈曲带涟漪.持竿不是因鲂鲤,要斫青光写楚辞.
看来,这位诗人的心态和我差不多,又及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结果是两样都当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人早就这么说过.
既如此,我的饮一口汨罗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归去罢,归去来兮,说不定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就是我明日的汨罗.
汪曾祺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自得耀眼.来了放蜂人.蜂箱都放好了,他
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
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
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
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
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
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
容不迫,慢条斯理的.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
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
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
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
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养蜂人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
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
服,买鞋,买饼干.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勾针给他勾一顶大红的毛线
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
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大,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
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
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选自《人间草木》)
一朵午荷 洛夫
这是去夏九月问的旧事,我们为了荷花与爱情的关系,曾发生过一次温和的争辩.“爱荷的人不但爱它花的娇美,叶的清香,枝的挺秀,也爱它夏天的喧哗,爱它秋季的寥落,甚至觉得连喂养它的那池污泥也污得有些道理.”
“花凋了呢?”
“爱它的翠叶田田.”“叶残了呢?”
“听打在上面的雨声呀!”
“这种结论岂不太过罗曼蒂克.”“你认为……?”
“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
记得那是一个落着小雨的下午,午睡醒来,突然想到去博物馆参观一位朋友的画展.为了喜欢那份凉意,手里的伞一直未曾撑开,冷雨溜进颈子里,竟会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喜.沿着南海路走过去,一辆红色计程车侧身驰过,溅了我一裤脚的泥水.抵达画廊时,正在口袋里乱掏,你突然在我面前出现,并递过来一块雪白的手帕.老是喜欢做一些平淡而又惊人的事,我心想.
这时,室外的雨势越来越大,群马奔腾,众鼓齐擂,整个世界茏罩在一阵阵激越的杀伐声中,但极度的喧嚣中又有着出奇的静.我们相偕跨进了面对植物园的阳台.“快过来看!”你靠着玻璃窗失神地叫着.我挨过去向窗外一瞧,顿时为窗下一幅自然的奇景所感动,怔住.窗下是一大片池荷,荷花多已凋谢,或者说多已雕塑成一个个结实的莲蓬.满池的青叶在雨中翻飞着,大者如鼓,小者如掌,雨粒劈头劈脸洒将下来,鼓声与掌声响成一片,节奏急迫而多变化,声势相当慑人.
我们印象中的荷一向是青叶如盖,俗气一点说是亭亭玉立,之所以亭亭,是因为它有那一把瘦长的腰身,风中款摆,韵致绝佳.但在雨中,荷是一群仰着脸的动物,专注而矜持,显得格外英姿勃发,矫健中另有一种娇媚.雨落在它们的脸上,开始水珠沿着中心滴溜溜地转,渐渐凝聚成一个水晶球,越向叶子的边沿扩展,水晶球也越旋越大,瘦弱的枝杆似乎已支持不住水球的重负,由旋转而左摇右晃,惊险万分.我们的眼睛越
睁越大,心跳加速,紧紧抓住窗棂的手掌沁出了汗水.猝然,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荷身一侧,哗啦一声,整个叶面上的水球倾泻而下,紧接着荷枝弹身而起,又恢复了原有的挺拔和矜持,我们也随之嘘了一口气.我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一片浓烟刚好将脸上尚未褪尽的红晕掩住.
也许由于过度紧张,也许由于天气阴郁,这天下午我除了在思索你那句“欣赏别人的孤寂是一种罪恶”的话外,一直到画廊关门,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
但我真正懂得荷,是在今年一个秋末的下午.这次我是诚心去植物园看荷的,心里有了准备,仍不免有些紧张.跨进园门,在石凳上坐憩一下,调整好呼吸后,再轻步向荷池走去.
噫!那些荷花呢?怎么又碰上花残季节,在等我的只剩下满池涌动的青叶,好大一拳的空虚向我袭来.花是没了,取代的只是几株枯干的莲蓬,黑黑瘦瘦,一副营养不良的身架,跟丰腴的荷叶对照之下,显得越发孤绝.这时突然想起我那首《众荷喧哗》中的诗句:“众荷喧哗/而你是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柔的一朵/……”
午后的园子很静,除了我别无游客.我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满池的青荷出神.众荷田田亭亭如故,但歌声已歇,盛况不再.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繁华与喧嚣,到处拥挤不堪;现在静下来了,剩下我独自坐在这里,抽烟,扔石子,看池中自己的倒影碎了,又拼合起来,情势逆转,现在已轮到残荷来欣赏我的孤寂了.想到这里,我竞有些赧然,甚至感到难堪起来.其实,孤寂也并不就是一种羞耻,
当有人在欣赏我的孤寂时,我绝不会认为他有任何罪过.朋友,这点你不要跟我辩,兴衰无非都是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今年花事已残,明年照样由根而茎而叶而花,仍然一大朵一大朵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接受人的赞赏与攀折,它却毫无顾忌地一脚踩污泥,一掌擎蓝天,激红着脸大声唱着“我是一朵盛开的莲”,唱完后不到几天,它又安静地退回到叶残花凋的自然运转过程中去接受另一次安排,等到第二年再来接唱.
扑扑尘土,站起身来,绕着荷池走了一圈,绕第二圈时,突然发现眼前红影一闪而没.我又回来绕了半匝,然后蹲下身子搜寻,在重重叠叠的荷叶掩盖中,终于找到了一朵将谢而未谢,却已冷寂无声的红莲,我惊喜得手足无措起来,这不正是去夏那挨我最近,最静,最最温柔的一朵吗?
(选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读本②?一朵午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有删节)
春风
林斤澜
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粱,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撤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臂腿,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
麦苗在霜冰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大毂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先自1980年4月8日《北京晚报》)
饮一口汨罗江
熊召政
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的诗史中,已经流了,两千多年.诗人如我辈,视之为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取它一瓢饮者,更是大有人在.当然,饮的不是玉液琼浆,而是在漫长的春秋中浊了又清,清了又浊的苦涩.这苦涩,比秋茶更酽.
这会儿,我正在汨罗江的岸边,掬起一杯浑黄得叫人失望的江水.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我可是千里奔驰特意赶来的啊!
脖子一扬,我,饮了一口汨罗.
立刻,我感觉到,就像有一条吐着芯子的蛇窜入我的喉管,冰凉而滑溜,在我肝胆心肺间穿行,如同在烟雨迷蒙的天气里穿过三峡的蛟龙.
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脸色难堪,埋怨说:“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这水太脏了.”我报以苦笑.
朋友继续说:“你们诗人都是疯子,不过,也像圣徒.恒河的水污染那么严重,圣徒们也是长途跋涉,非得跑到那里去喝一口.”
我得承认,朋友这么说,并不是讥笑我,他只是不理解.我的行囊中,带有青岛啤酒和可口可乐,为什么,我非得饮这浑黄的汨罗?
这小小的隔阂,让我想起禅家的一段公案.一次,著名禅师药山椎俨看到一个和尚,问:“你从哪里来?”和尚答:“我从湖南来.”药山又问:“湖水是不是在泛滥?”答:“湖水还没有泛滥.”药山接着说:“奇怪,下那么多雨,湖水为什么没有泛滥?”和尚对此没有满意的回答.因而药山的弟子云岩说:“是在泛滥.”同时,药山另一个弟子东山大叫道:“何劫中不曾泛滥!”细细品味这句话,不得不佩服禅家独特的思维品质.何水不脏?我想对朋友当头棒喝的这四个字,本源于何劫中不曾泛滥的追问.
不过,那四个字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然而由禅家推及诗家,我想得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滥,每个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节的湖水泛滥,又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呢?屈原淹死在汨罗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汨罗不只是湘北的这一条,也不尽然是由波涛组成,知道这一点的,恐怕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滥!还可以推补一句,何处没有汨罗江?
嵇康的汨罗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广陵散》;李白的汨罗江,是一片明月;苏东坡的汨罗江,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贬谪之骆;秋瑾的汨罗江,是一把砍头的大刀;闻一多的汨罗江,是一颗穿胸的子弹……到这里,我禁不住问自己:
你的汨罗江会是什么呢?
据考证,屈原本姓熊,是我的同宗.从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写诗做人的坐标.每当灾难来临,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汨罗江.好多次,当我的愤怒无法宣泄,我就想跑到这里来,跳进去,让汨罗再汨罗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这汨罗江的岸边,饮了一口浑黄后,我的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
江面上,二三渔舟以一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悠然,从我眼前飘过.不知道屈原为何许人也的渔翁,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五月的阳光.偶尔有几条鱼苗,看上去像二月的柳叶,也被渔翁扔进了鱼篓.那也是他的收获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渔翁之意,却是肯定在于鱼的.
中国的渔翁形象,从劝屈原“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惯看秋月春风”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权力更迭,人间兴废,与他们毫不相干.船头上一坐,就着明月,两三条小鱼,一壶酒,他们活的好逍遥啊!你看这条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汨罗江上,屈原早就不见了,而渔翁仍在.
这就是我的惆怅所在.一位清代的湖南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
萧瑟寒塘垂竹枝,长桥屈曲带涟漪.持竿不是因鲂鲤,要斫青光写楚辞.
看来,这位诗人的心态和我差不多,又及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结果是两样都当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人早就这么说过.
既如此,我的饮一口汨罗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归去罢,归去来兮,说不定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就是我明日的汨罗.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