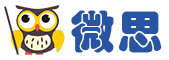问题描述:
要交关于庄子的《齐物论》的问题,大家帮我想想谢谢了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
陈 静
一
《庄子·齐物论》历来号称难读,难读有好几层意思,一是有的语词十分费解,例如“以言其老洫”的“老洫”,“奚必知代”的“知代”等等,当然可以根据上下文和历代注释选择或作出某种解释,但是这些语词的来头和含义毕竟是模糊的.二是有的句子即使在上下文中也很难确定其含义,例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故曰莫若以明”之类,就很难解释清楚.“莫若以明”,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译今注》译作“所以说不如用明净的心境去关照事物的实况”,“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陈先生译为“所以圣人不用(知见辩说)夸示于人而寄寓在各物自身的功分上”,都添加了很多东西.如果需要添加内容并且是实质性的内容才能解释一个句子,那么,为什么添加这些内容就是需要追问的了.其他难解的句子还有不少.读书不断地碰到这些沟沟坎坎,确实读不通畅.不过,《齐物论》难读的真正原因还不在于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在于它的“意”是在“言”外的,仅仅从文字的表面,很难把握住它深刻的内涵,因此,《齐物论》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字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下层结构,它的行文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在往前推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齐物论》认为是非无定,“正味”“正色”“正处”没有普遍的衡定的标准,只有在特定的对象关系中才有意义,主张以“因是因非”的“两行”去超越是非,这个主旨似乎不难把握.但是,因是因非为什么要从“吾丧我”说起呢?“三籁”与“吾丧我”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子綦在告诉子游“今者吾丧我”之后,要为他说人籁、地籁和天籁呢?主张“因是因非”的《齐物论》为什么要用“庄周梦蝶”这个美丽的预言来结束全篇,这个结尾与开篇的“吾丧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在初读《庄子·齐物论》时是有这许多困惑的,反复地读与思,终于想通了从前困惑不解的诸因素之间,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明白了其间的联系后,《齐物论》的思路也就浮现出来了:“吾丧我”提示着庄子对“吾”与“我”进行的分别,而这一分别是建立“因是因非”的超是非立场的前提;三籁之说一方面为理解吾、我的分别作铺垫,另一方面又提示“是非”产生的原由;庄周梦蝶以寓言的方式隐喻“吾”“我”的状态,并对开篇的“吾丧我”作出呼应.我认为,《齐物论》无论从思路上看还是从文气上看,都是一篇相当完整的论文,而解读它的关键,就是“吾丧我”.
二
吾、我在一般语境下都是第一人称代名词,在《论语》、《老子》、《孟子》和《庄子》里是混着用的.当然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用法上的一些小差别,例如在《论语》中,“吾”既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作自称代词,指“我,我的”,只有一次由第一义引申作“自以为是”的意义:毋我.并且,“吾”指代“我,我们”时,一般用作主语,若用作宾语,则只用于否定句中.[1] 又如在《老子》里,吾、我都有用作主语的例子,但是在表达主体意味更强烈的知、见、观等动作时,则往往用“吾”作主语,而需要第一人称作宾语时往往使用“我”.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是倾向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更不是概念性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吾、我之间用法上的这些差别而认为它们已经有了概念性的分别.
吾、我没有概念上的差别,同等地是第一人称代名词.但是在《庄子·齐物论》开篇的“吾丧我”这一特别的表述中, 庄子却是用这两个似乎相同的人称代词在指示着“人”的不同的存在状态.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尽管庄子用了“吾”“我”来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分别,但是即使在《齐物论》本篇,这种用法也不是固定的,在其他地方,吾、我往往又只是一般的人称代词了.我们说《庄子》难读的原因在于意在言外,而庄子的用语又往往十分随意,常常用“平常”的话,来表达“非常”的意思,这无疑使难读的《庄子》更加难读.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庄子用吾、我对“人”的存在状态作了什么样的分别.
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 的存在,永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中,相对于不同的对象,“我”又具体地展现为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作为形态的存在,“我”总是被动地陷溺于现实的困境之中,庄子说: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然疲役而不
知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
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是
芒者乎?
在庄子看来,“我”有形,是为“形态的我”,这个“形态的我”处于与外物纠缠的状态之中,被外物裹携着、冲击着,踉跄于人生之途而没有片刻止息,终生劳碌却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不堪却不知归属何处.“形态的我”展示了“人”作为“物”的存在状态,这样的“我”,实在是被动而无奈的.后来王充片面地夸大了庄子的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义为“物”,例如《论衡·论死篇》说:“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温篇》说:“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自纪篇》说:“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于“物”,就把人的灵性和主动性彻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里的人是极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间如同蚤虱附生于人的身上.在《论衡》里,“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变动篇》)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象王充这样理解“人”,当然不符合庄子的意思.在庄子眼里,人是有“物”的一面,物性的人,是为“形态的我”,然而人的这种物性的存在状态,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庄子才要说“丧我”.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我”并且只是这样一个“形态的我”,那么,“人”就不可能从“物”中超脱出来.人作为“人”,却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很可悲的.所以庄子在描述了“形态的我”的被动和无奈之后,一再感叹“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态的,也是情态的.所谓“情态的我”,是指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的“我”.这样的“我”,必定处于种种情景状态之下.所以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没有片刻宁静,“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或傲慢,或阴险,或慎密,“其发若机栝”,窥视着是非,“其留如诅盟”,严守着秘密.总之是不断地在“喜怒哀乐,虑叹变 ,姚佚启态”的不同情态中流转.在庄子对“情态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只是在说“我”在各种不同的情状下的表现,在说一个情态的“我”,但是,在他言说的这样一个“我”的背后,却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他人”来,因为“我”的种种情态,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为对象的.因此可以说,“情态的我”提示着一个“他人”的参照,从而展示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面.我们说过,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形态的我”,人是不可能从“物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越出来的,同样,如果人生只展现为一个“情态的我”,人也不可能从社会性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从“角色”中超脱出来.《史记》在记载庄周事迹时说: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诋訾孔子之徒”[2].庄子不满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人的社会属性绝对化,使人固着于角色的序列之中.经过儒家整理规范后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么是君,要么是臣,要么是父,要么是子,总之要在这个角色的序列中担当某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角色关系中,一个人所担当的角色是会有所不同的,例如面对父,他的角色是子,面对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一个角色,而决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为“人”.儒家的“人”是凭借“角色”而呈现的,儒家的圣人,一定是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担当的所有角色之“当然”的人.这正是庄子所反对的.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丧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为也就是“伪”的色彩,只有擦掉“伪”的色彩,从“情态的我”中超脱出来,真正的我才能呈现.真正的我,庄子称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丧我”这个吾、我对举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三
庄子提出了“吾”,却没有告诉我们“吾”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吾”如同“天籁”一样,是不可言说的.
我们看《齐物论》里子綦为子游说三籁,其实只是在地籁上说,当子游懂得了“地籁则众窍是已”,又自言“人籁则比竹是已”之后,他向子綦请问“敢问天籁”.面对子游的问题,子綦却不能用“天籁则x x是已”来回答,而只是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几乎是遁词.子綦不能用定义的句式或同一性的句式来答问,是因为天籁并不是人籁、地籁之外的另一个“什么”,用郭象的话来说,就是“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天籁只是一个“境界”,这种境界需要超越人籁和地籁去领悟.需要超越的东西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籁的成与亏和地籁的分与别.庄子说:
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
郭象注曰:
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炫,虽有繁手,遗声多矣.而
执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
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冯友兰先生解释说:
郭象在这里注说,……无论有多么大的管弦乐队,总不能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声音全奏出来,总有些声音被遗漏了.就奏
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有所成;就被遗漏的声音说,这是有所亏.
所以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就无成无亏.(见庄子哲学讨
论集)
因此,正是因为有“亏”,人籁才有“成”,因而成为“有”,同样,地籁也正是在众窍彼此有别的条件下才成为“有”的,而天籁之成为“有”,靠的却是对人籁之有成亏、地籁之有差别的揭示,天籁不能直接言说,只有通过说三籁而揭示人籁之有成亏和地籁之有差别来使“天籁”透露,天籁透显出来被领悟了,人籁的成亏、地籁的差别也就被超越了.
《齐物论》对三籁分辨,是为了把“吾”示给我们.如同“天籁”一样,“吾”也不能用“是”“什么”的句式来言说,而只能用否定的方式,靠否定“吾”就是“我”的方式来使之透显.“吾”不是“我”,不是形态的,也不是情态的.正因为吾不是形态的存在,所以人的形体或形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足以代表“吾”,庄子说:“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庄子·德充符》描述了许多“德全而形不全”的人,例如支离无唇、哀骀它、叔山无趾,王骀等,这些人或奇形怪状,或缺胳膊少腿,但像貌丑陋或断手缺腿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真我”或者“吾”与人的形貌没有关系.
“吾”不是“形态的我”,也不是“情态的我”,所以在任何极端的情景下都不为所动.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亟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超越了形态和情态的“吾”,“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是《庄子·逍遥游》的基本概念,它展示的是一个自由的境界.“我”被外物裹携且陷溺于角色的序列之中,与“游”无缘,“吾”才能“游”,“吾”的“游”展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的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了.
四
如果没有吾、我之分,人不可能从物性的和角色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当然也不能从“是非”中超越出来.
我们先对是非的含义稍加分辨.研究者们通常只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理解是非,把是非理解为对错,这种理解尽管不错,但是有片面之虞,因为庄子所说的是非,含义还要丰富得多.首先,是非有存在的含义:“是”,一定会“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但“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就必定“不是(非)”那样的一个“什么”,因此,庄子的是非,首先有“是或不是(非)什么”的含义.在这层含义上,才有什么“对”,什么“不对”的是非,才有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是非.前者是认识论意义的是非,后者是价值论意义的是非.认识论意义的是非(对错)和价值论意义的是非(好坏),都要以存在意义的是非(是这个、这样或那个、那样)为基础.住在潮湿的地方好,还是住在树巅上好,这要看居住者是谁,如果是泥鳅,那么是泥处好;如果是猿猴,那么是木处好;如果是人,则这两处都不好.何为正处,要根据处者为何来决定.正味、正色也是一样.在《齐物论》中,是非的三层含义是重叠在一起的,只是在具体的语境下,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我们理解了庄子的是非的丰富内涵,再来看为什么需要区分吾、我,人才可能从是非中超脱出来.
如果“人”只是一个“我”,那么,人一定是在是非的关系之中的.因为“我”一但“是这个或这样”,就必定“不是(非)那个或那样”;又因为“我”作为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纠缠于物性的和社会性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因此表现为“是这个或这样”的“我”,必定面临着它所“不是(非)”的“那个或那样”.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一但成为“有”,必定面临一个“他”;如果把“我”称为“此”,那么“我”所面对的“他”就是“彼”;如果以“我”为“是”,那么,“他”就为“非”.从“我”出发,就有了彼此和是非,所以庄子说“此亦一是非”,从他出发也一样,所以庄子又说“彼亦一是非”.是非又是无穷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我”,都可能面对无限多的“他”,形成彼此、是非的无限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庄子又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怎么样才能从是非的链条中解脱出来?庄子提出了“两行”,所谓两行,就是“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也就是用“可”的态度对待“可”,用“不可”的态度对待“不可”,用“然”的态度对待“然”,用“不然”的态度对待“不然”,这样的态度,庄子称之为“因是因非”.
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就“在”是非的关系之中,而“我”之所“在”,决定了“我”对待是非的态度:“我”既然是一个“是”,就只可能以“是”的态度来对待“是”和“非”,以“是”的态度对待“是”,就是“是其所是”,也就是“是”“是”,即“可乎可”,“然于然”;以“是”的态度对待“非”,就构成了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是非,而“不可乎不可”,“不然于不然”的态度,是一个“非”“非”的态度,这个态度,由“我”出发是建立不起来的.“我”只能持“是”的态度,由“我”出发,只能建立其“是”“非”的对立性态度.由此可见,“因是因非”的前提,就是要从他我、彼此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超脱出来.这时我们便看到了“吾”的意义,“吾”不是“我”,不是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作为“非形态的”存在,“吾”不会纠缠于“物”的关系之中;作为“非情态的”存在,“吾”不会纠缠于“社会”的关系之中.“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只有“吾”,能够做到“因是因非”.
“吾”是自由的.吾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让“我”“自在”,也让“他”“自在”,我与他皆得自在,由自在而自由,于是皆大欢喜.尧想讨伐宗、脍、胥敖三个小国,“南面而不释然”,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以“我”的立场来对待尚未开化的宗、脍和胥敖,想把文明强加在三个小国之上,从而陷入了是非之中.舜为他说阳光普照万物的道理,告诉他“德之进乎日者”是不分彼此、是非的.这是助他突破“我”的局限去领悟“吾”,并由此出发建立因是因非的态度.“我”必定是独断的,霸道的,“我”由独断、霸道出发,结果是陷入他我、彼此的是非之中而不得自由.只有“丧我”,使“吾”透显,才有宽容,才得自在-自由.
《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展示了一个自由的人生境界,第二篇《齐物论》告诉我们以“丧我显吾”的途径去实现.
《哲学研究》2001.5
http://philosophy.cass.cn/facu/chenjing/zhuangzi.htm
陈 静
一
《庄子·齐物论》历来号称难读,难读有好几层意思,一是有的语词十分费解,例如“以言其老洫”的“老洫”,“奚必知代”的“知代”等等,当然可以根据上下文和历代注释选择或作出某种解释,但是这些语词的来头和含义毕竟是模糊的.二是有的句子即使在上下文中也很难确定其含义,例如“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故曰莫若以明”之类,就很难解释清楚.“莫若以明”,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译今注》译作“所以说不如用明净的心境去关照事物的实况”,“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陈先生译为“所以圣人不用(知见辩说)夸示于人而寄寓在各物自身的功分上”,都添加了很多东西.如果需要添加内容并且是实质性的内容才能解释一个句子,那么,为什么添加这些内容就是需要追问的了.其他难解的句子还有不少.读书不断地碰到这些沟沟坎坎,确实读不通畅.不过,《齐物论》难读的真正原因还不在于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在于它的“意”是在“言”外的,仅仅从文字的表面,很难把握住它深刻的内涵,因此,《齐物论》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字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下层结构,它的行文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在往前推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齐物论》认为是非无定,“正味”“正色”“正处”没有普遍的衡定的标准,只有在特定的对象关系中才有意义,主张以“因是因非”的“两行”去超越是非,这个主旨似乎不难把握.但是,因是因非为什么要从“吾丧我”说起呢?“三籁”与“吾丧我”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子綦在告诉子游“今者吾丧我”之后,要为他说人籁、地籁和天籁呢?主张“因是因非”的《齐物论》为什么要用“庄周梦蝶”这个美丽的预言来结束全篇,这个结尾与开篇的“吾丧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在初读《庄子·齐物论》时是有这许多困惑的,反复地读与思,终于想通了从前困惑不解的诸因素之间,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明白了其间的联系后,《齐物论》的思路也就浮现出来了:“吾丧我”提示着庄子对“吾”与“我”进行的分别,而这一分别是建立“因是因非”的超是非立场的前提;三籁之说一方面为理解吾、我的分别作铺垫,另一方面又提示“是非”产生的原由;庄周梦蝶以寓言的方式隐喻“吾”“我”的状态,并对开篇的“吾丧我”作出呼应.我认为,《齐物论》无论从思路上看还是从文气上看,都是一篇相当完整的论文,而解读它的关键,就是“吾丧我”.
二
吾、我在一般语境下都是第一人称代名词,在《论语》、《老子》、《孟子》和《庄子》里是混着用的.当然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用法上的一些小差别,例如在《论语》中,“吾”既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作自称代词,指“我,我的”,只有一次由第一义引申作“自以为是”的意义:毋我.并且,“吾”指代“我,我们”时,一般用作主语,若用作宾语,则只用于否定句中.[1] 又如在《老子》里,吾、我都有用作主语的例子,但是在表达主体意味更强烈的知、见、观等动作时,则往往用“吾”作主语,而需要第一人称作宾语时往往使用“我”.尽管有这些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是倾向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更不是概念性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吾、我之间用法上的这些差别而认为它们已经有了概念性的分别.
吾、我没有概念上的差别,同等地是第一人称代名词.但是在《庄子·齐物论》开篇的“吾丧我”这一特别的表述中, 庄子却是用这两个似乎相同的人称代词在指示着“人”的不同的存在状态.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尽管庄子用了“吾”“我”来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分别,但是即使在《齐物论》本篇,这种用法也不是固定的,在其他地方,吾、我往往又只是一般的人称代词了.我们说《庄子》难读的原因在于意在言外,而庄子的用语又往往十分随意,常常用“平常”的话,来表达“非常”的意思,这无疑使难读的《庄子》更加难读.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庄子用吾、我对“人”的存在状态作了什么样的分别.
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 的存在,永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中,相对于不同的对象,“我”又具体地展现为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作为形态的存在,“我”总是被动地陷溺于现实的困境之中,庄子说: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然疲役而不
知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
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是
芒者乎?
在庄子看来,“我”有形,是为“形态的我”,这个“形态的我”处于与外物纠缠的状态之中,被外物裹携着、冲击着,踉跄于人生之途而没有片刻止息,终生劳碌却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不堪却不知归属何处.“形态的我”展示了“人”作为“物”的存在状态,这样的“我”,实在是被动而无奈的.后来王充片面地夸大了庄子的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义为“物”,例如《论衡·论死篇》说:“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温篇》说:“人禽皆物也,俱为万物.”《自纪篇》说:“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于“物”,就把人的灵性和主动性彻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里的人是极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间如同蚤虱附生于人的身上.在《论衡》里,“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变动篇》)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象王充这样理解“人”,当然不符合庄子的意思.在庄子眼里,人是有“物”的一面,物性的人,是为“形态的我”,然而人的这种物性的存在状态,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庄子才要说“丧我”.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我”并且只是这样一个“形态的我”,那么,“人”就不可能从“物”中超脱出来.人作为“人”,却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很可悲的.所以庄子在描述了“形态的我”的被动和无奈之后,一再感叹“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态的,也是情态的.所谓“情态的我”,是指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的“我”.这样的“我”,必定处于种种情景状态之下.所以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没有片刻宁静,“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或傲慢,或阴险,或慎密,“其发若机栝”,窥视着是非,“其留如诅盟”,严守着秘密.总之是不断地在“喜怒哀乐,虑叹变 ,姚佚启态”的不同情态中流转.在庄子对“情态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只是在说“我”在各种不同的情状下的表现,在说一个情态的“我”,但是,在他言说的这样一个“我”的背后,却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他人”来,因为“我”的种种情态,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为对象的.因此可以说,“情态的我”提示着一个“他人”的参照,从而展示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一面.我们说过,如果人生就展现为一个“形态的我”,人是不可能从“物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越出来的,同样,如果人生只展现为一个“情态的我”,人也不可能从社会性的存在状态或者说从“角色”中超脱出来.《史记》在记载庄周事迹时说: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诋訾孔子之徒”[2].庄子不满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人的社会属性绝对化,使人固着于角色的序列之中.经过儒家整理规范后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么是君,要么是臣,要么是父,要么是子,总之要在这个角色的序列中担当某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角色关系中,一个人所担当的角色是会有所不同的,例如面对父,他的角色是子,面对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一个角色,而决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为“人”.儒家的“人”是凭借“角色”而呈现的,儒家的圣人,一定是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担当的所有角色之“当然”的人.这正是庄子所反对的.在庄子看来,“情态的我”丧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为也就是“伪”的色彩,只有擦掉“伪”的色彩,从“情态的我”中超脱出来,真正的我才能呈现.真正的我,庄子称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丧我”这个吾、我对举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三
庄子提出了“吾”,却没有告诉我们“吾”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吾”如同“天籁”一样,是不可言说的.
我们看《齐物论》里子綦为子游说三籁,其实只是在地籁上说,当子游懂得了“地籁则众窍是已”,又自言“人籁则比竹是已”之后,他向子綦请问“敢问天籁”.面对子游的问题,子綦却不能用“天籁则x x是已”来回答,而只是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几乎是遁词.子綦不能用定义的句式或同一性的句式来答问,是因为天籁并不是人籁、地籁之外的另一个“什么”,用郭象的话来说,就是“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天籁只是一个“境界”,这种境界需要超越人籁和地籁去领悟.需要超越的东西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籁的成与亏和地籁的分与别.庄子说:
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
郭象注曰:
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炫,虽有繁手,遗声多矣.而
执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
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冯友兰先生解释说:
郭象在这里注说,……无论有多么大的管弦乐队,总不能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声音全奏出来,总有些声音被遗漏了.就奏
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有所成;就被遗漏的声音说,这是有所亏.
所以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就无成无亏.(见庄子哲学讨
论集)
因此,正是因为有“亏”,人籁才有“成”,因而成为“有”,同样,地籁也正是在众窍彼此有别的条件下才成为“有”的,而天籁之成为“有”,靠的却是对人籁之有成亏、地籁之有差别的揭示,天籁不能直接言说,只有通过说三籁而揭示人籁之有成亏和地籁之有差别来使“天籁”透露,天籁透显出来被领悟了,人籁的成亏、地籁的差别也就被超越了.
《齐物论》对三籁分辨,是为了把“吾”示给我们.如同“天籁”一样,“吾”也不能用“是”“什么”的句式来言说,而只能用否定的方式,靠否定“吾”就是“我”的方式来使之透显.“吾”不是“我”,不是形态的,也不是情态的.正因为吾不是形态的存在,所以人的形体或形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足以代表“吾”,庄子说:“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庄子·德充符》描述了许多“德全而形不全”的人,例如支离无唇、哀骀它、叔山无趾,王骀等,这些人或奇形怪状,或缺胳膊少腿,但像貌丑陋或断手缺腿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真我”或者“吾”与人的形貌没有关系.
“吾”不是“形态的我”,也不是“情态的我”,所以在任何极端的情景下都不为所动.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亟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超越了形态和情态的“吾”,“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是《庄子·逍遥游》的基本概念,它展示的是一个自由的境界.“我”被外物裹携且陷溺于角色的序列之中,与“游”无缘,“吾”才能“游”,“吾”的“游”展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的和“角色”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了.
四
如果没有吾、我之分,人不可能从物性的和角色性的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当然也不能从“是非”中超越出来.
我们先对是非的含义稍加分辨.研究者们通常只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理解是非,把是非理解为对错,这种理解尽管不错,但是有片面之虞,因为庄子所说的是非,含义还要丰富得多.首先,是非有存在的含义:“是”,一定会“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但“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就必定“不是(非)”那样的一个“什么”,因此,庄子的是非,首先有“是或不是(非)什么”的含义.在这层含义上,才有什么“对”,什么“不对”的是非,才有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是非.前者是认识论意义的是非,后者是价值论意义的是非.认识论意义的是非(对错)和价值论意义的是非(好坏),都要以存在意义的是非(是这个、这样或那个、那样)为基础.住在潮湿的地方好,还是住在树巅上好,这要看居住者是谁,如果是泥鳅,那么是泥处好;如果是猿猴,那么是木处好;如果是人,则这两处都不好.何为正处,要根据处者为何来决定.正味、正色也是一样.在《齐物论》中,是非的三层含义是重叠在一起的,只是在具体的语境下,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我们理解了庄子的是非的丰富内涵,再来看为什么需要区分吾、我,人才可能从是非中超脱出来.
如果“人”只是一个“我”,那么,人一定是在是非的关系之中的.因为“我”一但“是这个或这样”,就必定“不是(非)那个或那样”;又因为“我”作为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纠缠于物性的和社会性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因此表现为“是这个或这样”的“我”,必定面临着它所“不是(非)”的“那个或那样”.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一但成为“有”,必定面临一个“他”;如果把“我”称为“此”,那么“我”所面对的“他”就是“彼”;如果以“我”为“是”,那么,“他”就为“非”.从“我”出发,就有了彼此和是非,所以庄子说“此亦一是非”,从他出发也一样,所以庄子又说“彼亦一是非”.是非又是无穷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我”,都可能面对无限多的“他”,形成彼此、是非的无限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庄子又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怎么样才能从是非的链条中解脱出来?庄子提出了“两行”,所谓两行,就是“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也就是用“可”的态度对待“可”,用“不可”的态度对待“不可”,用“然”的态度对待“然”,用“不然”的态度对待“不然”,这样的态度,庄子称之为“因是因非”.
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就“在”是非的关系之中,而“我”之所“在”,决定了“我”对待是非的态度:“我”既然是一个“是”,就只可能以“是”的态度来对待“是”和“非”,以“是”的态度对待“是”,就是“是其所是”,也就是“是”“是”,即“可乎可”,“然于然”;以“是”的态度对待“非”,就构成了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是非,而“不可乎不可”,“不然于不然”的态度,是一个“非”“非”的态度,这个态度,由“我”出发是建立不起来的.“我”只能持“是”的态度,由“我”出发,只能建立其“是”“非”的对立性态度.由此可见,“因是因非”的前提,就是要从他我、彼此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超脱出来.这时我们便看到了“吾”的意义,“吾”不是“我”,不是形态的和情态的存在,作为“非形态的”存在,“吾”不会纠缠于“物”的关系之中;作为“非情态的”存在,“吾”不会纠缠于“社会”的关系之中.“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只有“吾”,能够做到“因是因非”.
“吾”是自由的.吾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让“我”“自在”,也让“他”“自在”,我与他皆得自在,由自在而自由,于是皆大欢喜.尧想讨伐宗、脍、胥敖三个小国,“南面而不释然”,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以“我”的立场来对待尚未开化的宗、脍和胥敖,想把文明强加在三个小国之上,从而陷入了是非之中.舜为他说阳光普照万物的道理,告诉他“德之进乎日者”是不分彼此、是非的.这是助他突破“我”的局限去领悟“吾”,并由此出发建立因是因非的态度.“我”必定是独断的,霸道的,“我”由独断、霸道出发,结果是陷入他我、彼此的是非之中而不得自由.只有“丧我”,使“吾”透显,才有宽容,才得自在-自由.
《庄子》第一篇《逍遥游》展示了一个自由的人生境界,第二篇《齐物论》告诉我们以“丧我显吾”的途径去实现.
《哲学研究》2001.5
http://philosophy.cass.cn/facu/chenjing/zhuangzi.htm
展开全文阅读